卡尔·波兰尼《大转型》连载——译者序
“唯有抛弃市场社会的乌托邦,我们才能直面社会的现实。”
译者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是一部罕见的学术经典,它超越了单一学科的藩篱,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哲学洞见,探究了19世纪文明的兴衰及其崩溃对20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影响。
本书虽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之中(1944年首次出版),但其对市场、社会与人类自由关系的剖析,至今仍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全球化危机、社会撕裂与制度变革,提供了最为启迪人心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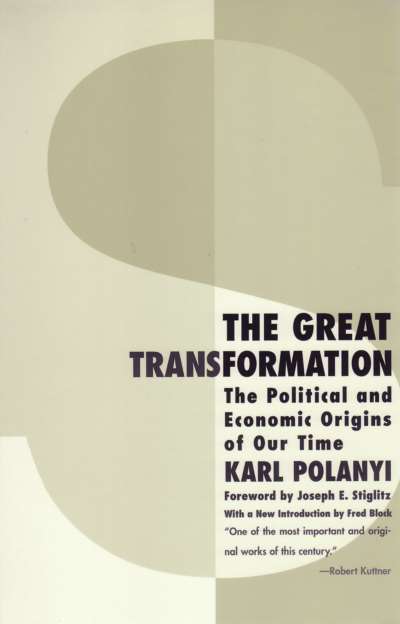
一、市场乌托邦的崩溃与“双向运动”
波兰尼的核心论点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彻底的乌托邦”之上。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质上非商品的社会要素强行转化为“虚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并将其置于市场机制的无情支配之下。
当“市场规律”成为人类命运、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唯一裁决者时,资本逻辑便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殖民。结果是:人的劳动被抽象化,自然被商品化,社会关系被异化为货币关系。
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的扩张总会激起反抗。波兰尼称这种反抗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是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为捍卫人类生存与尊严而展开的自发抵抗。市场的单向扩张与社会的反向保护构成了他著名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这一持续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经济制度试图将社会“脱嵌”(disembed)于人类共同体之上,而社会则不断试图重新嵌入(re-embed)经济过程,使之回归人的控制。正是这种历史的拉锯,最终导致了19世纪自由放任秩序的崩溃,并催生出法西斯主义、新政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不同的制度性“再嵌入”形式。
二、从制度困境到哲学困境
波兰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止步于经济史或政治史的层面,而是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对“自由”的抽象化理解——它将自由定义为摆脱一切“外在干预”的市场行为,从而将社会规划与国家调控视为对自由的压制。
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理解为摆脱一切强制的个体自主,把市场视为“无权力”的领域。
然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资本摆脱社会干预、以经济强制取代政治强制的自由。市场的“中立性”只是掩盖权力关系的幻象。波兰尼正是以历史实证揭穿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在市场社会中,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力被伪装成“交换的自由”,而失业与贫困被归咎于个人选择。
三、自由的重生与“对现实的接受”
波兰尼提出,人类必须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重新定义自由。这一新的自由不是拒绝权力,而是通过自觉的社会规划和公共制度,使权力成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手段。
他所说的对“现实的顺从”(resignation),绝非宿命式的妥协,而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清醒认知:它要求承认权力与稀缺的客观存在,以及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约束与冲突。唯有在此坚实的承认之上,人类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全部斗争力量投向消除所有可消除的不公正。
当人类不再畏惧权力本身,而是以集体的理性与组织来驾驭它时,计划与调控便不再是自由的敌人,而成为保障与扩展自由的制度条件。这正是波兰尼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自由的内涵。
对中国读者而言,《大转型》提供了三重镜鉴。
其一,是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化转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见证了效率的飞跃与财富的激增,也目睹了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与城乡断裂的阵痛。波兰尼提醒我们,市场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其扩张必然伴随社会的“脱嵌”风险。当教育、医疗、住房被彻底商品化,当算法与资本联手重塑劳动关系,我们是否也在无意中制造了新的“虚构商品”?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增长与稳定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正是波兰尼留给我们的时代课题。
其二,是对“保护性反运动”的历史省察。
波兰尼认为,社会的自我保护并非反市场的盲动,而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在中国语境下,土地制度、户籍政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体系,无不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对市场力量的某种“再嵌入”努力。然而,这些保护机制本身也可能异化:当反运动诉诸威权管控而非民主协商,当保护之名被官僚集团利用,我们便可能偏离波兰尼所期许的“自由本质”——一种不仅免于匮乏,更能积极参与共同体生活的自由。
其三,是对全球化命运共同体的警醒。
波兰尼写作之际,世界正从19世纪的“百年和平”滑向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今日之中美博弈、气候危机与数字霸权,何尝不是新一轮“大转型”的阵痛?当供应链断裂、通胀失控与地缘冲突交织,市场社会的脆弱性再度暴露。波兰尼的警告振聋发聩:若任由市场逻辑吞噬政治与伦理,人类将再次为自己的发明付出惨痛代价。
《大转型》的中文译本已有多个版本,质量参差不齐。重新翻译或润色此书的念头,正源于对学术精确性与思想深度的追求。最初我仅计划在现有无版权译本基础上修订错漏,然而事实证明,这几乎等同于重新翻译整部著作。幸赖多种正式出版物的参照(如黄树民先生的译作,虽然两个“经济学家”在豆瓣炫耀其译作,并以此贬低黄先生),我得以在忠实原著与中文表达的通达性之间取得平衡。表面上波兰尼的文风常被诟病为“晦涩”,实则源于其跨学科的雄心:他既要与经济学家对话,又要向人类学家借力;既要剖析制度,又要捕捉文化脉动。在翻译过程中我保留了原文的复杂句式与概念张力,同时对关键术语进行了统一与注解。部分章节因涉及19世纪英国史而显得疏离,我特意增补脚注,以期拉近与中国读者的历史想象。
最后,谨以波兰尼的一句话献给所有翻开本书的读者:“唯有抛弃市场社会的乌托邦,我们才能直面社会的现实。”愿我们在市场与社会的永恒博弈中,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夏冬
2025年10月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