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激进革命?or 渐进改革?
要想获得渐进改革的时间,就必须腾出彻底改革的空间,倘若既要又要,既希望获得渐进的时间,又不愿意开辟主动让利的空间,那所谓的改革,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革命的催化剂。可惜在阶级社会,当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时,是不可能自我割肉到“双方满意”程度的……
激进的革命,还是渐进的改革?这个问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精英们所热爱的辩经话题,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于改革和革命,引述了一段对马克思观点的概括,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但不反对改革,仅反对改良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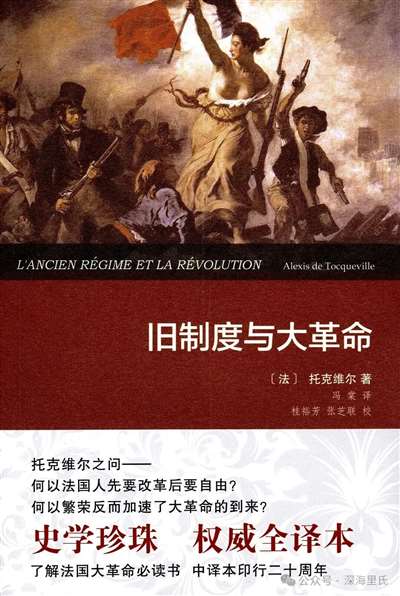
当然,对于这一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曾于1851年,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后的隐居时光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论述。这本著作也曾经被某个知名人物所推荐,引发了一波阅读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绝非简单的革命史著作,而是一部穿透时空的社会病理分析。当多数人将法国大革命归因于 “旧制度的极端腐朽” 时,托克维尔却抛出颠覆性观点:大革命的爆发,恰是旧制度启动改革之后 —— 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改革、行政松动,非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因 “特权阶层的顽固抵抗” 与 “民众期待的落空”,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种 “改革催生革命” 的悖论,正是理解 “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 辩证关系的关键钥匙。
托克维尔笔下的 “旧制度”,是 18 世纪法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地方自治被瓦解,贵族逐渐从 “地方管理者” 退化为 “宫廷寄生虫”—— 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公共责任,却顽固坚守免税、垄断官职等特权;农民成为唯一承担赋税与劳役的阶层,却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承受着物价上涨与土地兼并的双重挤压;新兴资产阶级虽拥有财富,却因无法突破等级壁垒,对旧制度既依赖又不满。

更具悲剧性的是改革的进程。路易十五后期至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已意识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性:1774 年杜尔哥推行改革,试图取消贵族免税权、规范税收;1787 年卡隆会议、1788 年三级会议的召集,均是为了打破特权僵局。但这些改革触碰了贵族与教士的核心利益 —— 巴黎高等法院公开反对,各省贵族联名抗议,最终改革沦为 “半吊子工程”。
民众看到了 “平等的可能”,却仍被束缚在旧特权的枷锁中,不满情绪最终转化为革命的洪流。托克维尔尖锐指出:“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社会开始改革的时刻”,旧制度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既失去了 “传统的合法性”,又无力构建 “改革的合理性”,最终只能在激进革命中崩塌。
托克维尔撰写此书时,正处于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 “百年革命周期”:1789 年大革命后,法国经历了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最终在 1851 年迎来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政变。作为亲历者,托克维尔目睹了 “激进革命的循环”—— 每次革命都试图彻底摧毁旧秩序,却屡屡陷入 “暴力替代暴力” 的困境: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拿破仑的对外扩张、1848 年革命后的街头流血,都让他反思:为何法国始终无法走出 “革命 - 动荡 - 复辟” 的怪圈?

这种个人经历,让《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充满现实情怀。托克维尔并非否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是追问:为何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转型?他的答案指向 “中间阶层的缺失”—— 旧制度下,贵族放弃了公共责任,资产阶级依附于王权,没有形成类似英国议会那样的 “缓冲力量”,导致社会矛盾只能通过激进革命释放。这种反思,既是对法国历史的总结,也是对 19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的警示。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古今历史中均可找到呼应。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的选择,从来不是 “道德偏好”,而是 “社会矛盾与改革能力” 的匹配结果。
法国大革命是激进革命的典型,但其代价是长期动荡 —— 从 1789 年到 1875 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法国用了 86 年才完成政治稳定,期间经历了 5 次革命、2 次帝国、3 次王朝复辟。反观英国,1688 年 “光荣革命” 后,通过渐进改革实现了社会转型:1832 年议会改革,给予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选举权;1867 年改革,扩大工人阶级参政范围;1884 年改革,基本实现成年男性普选。

这种 “阶梯式改革” 的关键,在于英国保留了议会这一 “中间机制”—— 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能够在议会框架内协商利益,避免了矛盾的极端化。
另一典型是普鲁士的 “俾斯麦改革”。19 世纪中叶,普鲁士面临民族统一与社会矛盾的双重压力,俾斯麦通过 “王朝战争” 完成统一后,推行渐进的社会改革:1883 年《疾病保险法》、1884 年《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 年《老年及残废保险法》,用社会保障体系缓和阶级矛盾,既维护了容克贵族的统治,又为德国工业化创造了稳定环境。这些史实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当统治阶层具备 “主动让利” 的改革能力,且存在 “利益协商机制” 时,渐进改革往往是成本更低的选择。

换句话说,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改革者真心愿意改革,具备主动让利的态度和能力,而不是摆出一副口惠而实不至的姿态。
最具代表性的反例,就是清末新政(1901-1911 年)—— 它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改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甲午战争后,清廷意识到旧制度的危机,推行废科举(1905 年)、改官制(1906 年)、练新军(1903 年)、预备立宪(1908 年)等改革。但这些改革同样陷入 “半吊子” 困境:1911 年 “皇族内阁” 暴露了满族权贵 “演都不想演” 的本质,地方士绅与资产阶级对改革彻底失望,最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廷迅速崩塌。

《旧制度与大革命》,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并非 “非此即彼” 的对立,而是社会转型的 “两种可能路径”。当改革能够及时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当特权阶层愿意放弃部分利益,当社会存在有效的协商机制时,渐进改革往往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进步 —— 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普鲁士的俾斯麦改革;而当改革停滞、特权固化、矛盾积累到临界点时,激进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 如法国大革命、清末辛亥革命。
托克维尔的价值,不在于否定革命,而在于给世界一种启示:避免激进革命的最佳方式,是推动及时、彻底的渐进改革。彻底和渐进,并不是一副对立的形容词,而是相伴相随的过程。
简而言之,要想获得渐进改革的时间,就必须腾出彻底改革的空间,倘若既要又要,既希望获得渐进的时间,又不愿意开辟主动让利的空间,那所谓的改革,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革命的催化剂。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