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的惊雷与闪电|人境院第二届写作研修班学员结业论文选登(7)
在今天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如何去启发重回小D和阿Q时代的群众,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认识刘老师和开始阅读刘老师的作品,缘于2023年12月26日在韶山冲参加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暨《黑与白》读者交流会,那时聆听了刘老师写作《黑与白》的心路历程,感受深刻,对一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敢于用笔作枪,为人民写作,十分钦佩。2025年年初又参加了人境院组织的为期半年的写作研修班,刘老师亲自为我们授课,使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更加深刻。早就想写一点东西,但苦于理解浅薄,文笔粗陋,迟迟不敢下笔。借这此结业作业的机会,我斗胆写一些自己的心得,谈一点体会,以表达我对刘老师的崇敬,同时,也要向刘老师学习,拿起手中的笔,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呐喊;用手中的笔,去作投枪,与一切黑暗作不屈的斗争。
一、忏悔还是不忏悔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利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可以使政治宣传“效力很大”;而作为革命工作者,要利用各种机会,将这些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在转战赣南建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红四军制定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能够进行化装宣传。这种化装宣传可以理解为一种情景演出,通过这种情景演出,让老百姓能够产生共鸣。1936年,毛泽东为丁玲的题词反映了其对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者重要性的认知,他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见毛泽东认为文艺作品的效力不亚于一支军队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将文化事业上升到和政治与军事同等重要的高度,注重文艺工作者及其创作的文艺作品在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注重培养拥有人民立场的文艺工作者。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了两次重要讲话,在第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讲到了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还有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谈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和如何普及的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可以说,主席的讲话为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步指明了清晰的发展方向,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的正确路径。很多文艺工作者以毛泽东的讲话为基本遵循,创作了大量的深得人心、揭露反动政府和社会黑暗、歌颂党和劳动人民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共产党推翻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几十年进程中,毛泽东思想被弃之如敝履。一些文艺创作者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背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他们进行所谓的忏悔,主动与过去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线精神进行切割,正是这种切割,他们迎来了资本和官僚的拥抱。历史已证明他们不过只是一些革命的投机客,他们的这种投机行为定将钉在耻辱柱上。而那些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文艺工作者被边缘化,有的还遭到了各种残酷的打压。如果我们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现象,这不正是两条路线在文艺界斗争的体现吗?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忏悔者”风光了,留下了充斥他们那个阶级情调的文艺作品,而因为他们已经远离工农大众,反映劳动人民工农大众的作品乏善可陈,甚至他们还要踏上一脚,或明或暗地恶毒地诅咒和抹黑毛泽东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些“不忏悔者”们,依然坚守自己的执着,笔耕不辍,为人民呐喊,虽遇千难而不折,同时,他们也在为人民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革命终结了吗?还是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如何用手中的笔去写一部劳动人民的历史?
刘老师虽不是“不忏悔者”中的一员,但却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长期的写作和社会经历中,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关注底层人民的辛酸苦辣,也关注着资本世界的血腥和狰狞。从他的长篇小说《人境》和《黑与白》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内心,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作者是有一个转变和决裂的。而这些小说的完成,便昭告了刘老师思想的升华,这是对“忏悔者”的回应,也是对“不忏悔者”的响应,更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践行。
二、《人境》:人应活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人境》折射出时代变迁给中国民众思想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作品既描写了农民在人民公社解散后的各种变化,也描写了国企工人在面临下岗买断时的不屈抗争,同时也对觉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商人的勾心斗角见利忘义进行了细致刻画,并对各级官僚们的形象勾勒描摹。小说场域宏大,让人窥见一个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一些时代场景细节的描写,能让人身临其境回到那个历史当中。作者深切关注中国社会,通过书中的不同角色并运用各种贴近时代的细节特写将这种变迁一一呈现出来,使得读者一进入小说中就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尤其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从书中都能找到自己曾见的影子,曾闻的声音,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能从中窥见时代的真实痕迹,并体会到作者深厚的人民情怀和扎实的还原生活的功夫。小说让我的心跳与历史融合在一起,思绪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能从小说中去考察一些历史的真相。而从小说中考据出的历史更加立体生动,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看完小说,还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小说映衬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之不易,让我们感受到创业艰辛,守业更加艰辛。
马垃是《人境》的一位主人公,他一生经历诸多坎坷,虽被社会大洪流所裹卷沉浮,心中始终有一束光,认定了人生的抱负后,便矢志不渝,坚持奋斗。小说以马垃的奋斗历程为明线,众多个性分明的人物如众星一般簇拥在他的周围,勾勒出那个时代的众生相。同时小说又以中国时代的变迁为暗线,对国家的每一步变化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真实的写生,绘就出深层次汹涌澎湃的社会发展历史画卷。这一明一暗,相互交织,相互呼应,使得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充满血肉,而不是孤淡寡味,形如枯槁,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经,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纬去钩织事物整体和立体的面,从而能够用细腻的笔去全面发掘事物背后的逻辑规律,为小说奠定了富有深度,令人深思的深厚思想根基。
小说还有一位主角,就是知识分子慕容秋,她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改开后回城参加高考改变人生轨迹,再成为高校的一位教授,很符合当时知识青年的成长脉络。慕容秋对神皇洲是充满感情的,因为她把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而且在那里她遇上了自己爱慕的对象,那就是马垃的哥哥马坷——一位毛泽东时代优秀的农村青年社员,但是让人痛苦的是,这么优秀的一位青年,在拯救集体财产时英勇牺牲了。而马垃的哥哥,何尝又不是小说的另一位主角,从马垃和慕容秋身上,我们都能或多或少感受到马坷的思想,当然,马垃更多的是一种传承,而慕容秋则是一种共鸣,这一点可以从慕容秋在马坷墓前的独白感受出来,她说:“坷子,……,只有在我心中,你永远那么英气勃勃,公而忘私,富于理想……”。我想,这就是一种境界吧,可是这种境界只在一个短暂的时代成为人们的标杆,而这短暂的时代,便是劳动人民的天堂。
从小说中,我们随着马垃和慕容秋的视角,不断转换,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诞生。一个时代的结束,则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经历了短暂八十年初的过渡,另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诞生了,仿佛天壤之别,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那么不可思议。作为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我还能感受到一点点毛泽东时代的美好气息,但很快这个气息便变成了窒息,国企改制使得父母下岗,满街的录像厅和游戏厅荼毒着寻求解放思想的人们,社会上成群的打锣(我们家乡称流氓为打锣)的人,藏在班车、火车和菜市场里的扒子手,难以遏制的环境污染,吸毒娼妓梅毒小广告复生,繁多的各种农村提留和残忍的计划生育,像铺天盖地的黑幕压过来,至今我想到那个时期,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愤怒和胸闷。看了刘老师的小说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为他写的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是用艺术的笔将其浓缩在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中。而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一个人民的立场,有一个人民的情怀,坚定着为人民写作的方向,去弘扬真善美,去鞭挞假恶丑。
三、《黑与白》:革命的艰辛与守成的艰难
刘老师的另一部巨著是《黑与白》,用老师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通过顾筝、王晟、杜威等中心人物的生活轨迹及其衍生出的错综复杂社会关系,聚集了上至庙堂中枢下至底层草根的社会各阶层典型人物,聚焦了百年中国史尤其是改开史的重大事件,勾勒出涵盖城乡朝野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时代潮汐与人物命运交相辉映,腐朽沉沦与亢进奋起激烈碰撞,黑与白、美与丑、善与恶交织,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人间活剧。
正如千人千面,为什么读者读同一部小说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是不是因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很多人会结合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经历将自己融入到小说的人物情节中去?正如同一时辰出生的人为什么命运会不一样,那是因为这些人出生的环境、成长的环境都大相径庭,而环境对一个人命运影响至关重要。我想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阅读完《黑与白》后,我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写一点体会,从人物性格去写,有很多人已经写了;从文章构思去写,我也不是学文艺相关专业的,所以总是感觉捉襟见肘,迟迟是交不出作业。但是,一些人物久久在我脑海中萦绕,不能离去。心中始终想着,要写一点东西。
《黑与白》和《人境》一样,都写了一个时代的变化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流中,小说中的人物的年龄,相貌甚至性格都在发生着变化,他们要么与变化的社会,要么与过去的自己,要么与他人之间,发生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交织碰撞构成了小说的故事情节。《黑与白》相比《人境》所展现的时间流更长,因而其中的矛盾就更加错综复杂,而且它横跨了一个地方的党的历史,并将党史作为一条极易忽略的重要线索埋在作品中,需要读者从另一个视角去深入理解。由此我们也能够想到这其中的情节冲突会有多少,也就意味着《黑与白》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图卷。
这条重要的党史线索并未简单复制一般党史的辉煌,而是充满着什么是革命?为什么革命?忠诚理想还是出卖同志等需要人们慎重思考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小说中未必给出确定的答案,更多是让读者去思考。比如宋乾坤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出卖同志,背叛革命?由于线索的中断,这成了永远的迷。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革命力量正是因为党内叛徒的投机和出卖而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且这样的叛徒可能占据高位,继续做着投机的勾当,迫害那些希望继续革命的战士。正如书中八路军干部的提问:“你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这个问题穿越时空,历久弥新,至今仍然是如雷如电,直刺人心。在这里,我不禁想到孔庆东老师在谈到《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时讲,假设甫志高这样的人没有被捕,他们进入到新中国之后,窃居党内重要位置,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呢?我们党内有多少像宋乾坤和甫志高这样的人呢?这是革命者和革命群众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去面对的重大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革命先觉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先觉者总要比人民群众站高望远,而人民群众很多时候觉悟认识是不高的。鲁迅曾批判过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处都是小D、阿Q、吴妈这样的群众,对中国国民曾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叹,而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说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听长辈说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是改开后,群众素质又一下跌入到低谷,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浸染下还要更差。在今天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如何去启发重回小D和阿Q时代的群众,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四、结语
刘老师的《人境》和《黑与白》,饱含着作家对人民的情怀,这是他践行毛泽东文艺“为什么人”问题的最好注解,见证了他“从‘个人’回到‘人民’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也意味着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声惊雷,喊出了中国左翼文学力量的新声;同时也是一道闪电,撕裂了”纯文学“陈腐的旧幕,展露出了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的那一片璀璨夺目的星海。我们坚信,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会有更多的左翼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劳动人民能够再次重回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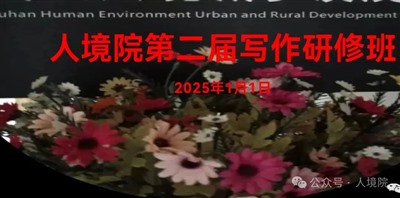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