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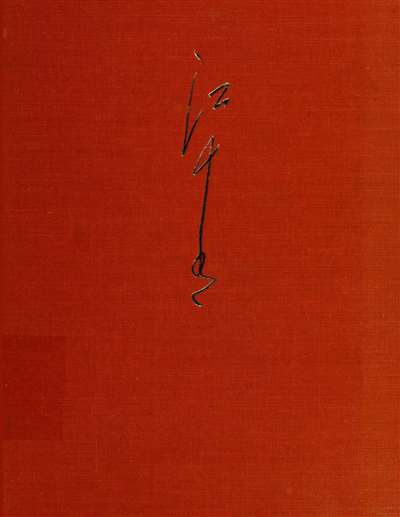
(接上)前情介绍:李进同志(一)邂逅
四
尽管我没指望再见到江青,但她的形象——充满挑战和变幻莫测——却顽固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要向别人公正地描述她的过去,她自己投射出的那些关于她早期那段基本模糊的生活以及她日益卷入历史洪流的光束是远远不够的,它们更多的是引人遐想,而非澄清事实。她只是四亿女性中的一员。然而我却觉得,她那将平凡与非凡融为一体的独特经历,为理解革命时期的中国女性与权力之间最根本的困境提供了线索。
与江青初次见面的第二天早上,我恢复了与邓颖超及其他妇女领导人的讨论。我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四个上午。和她的丈夫周恩来一样,邓颖超掌握着大量信息,并且能够用比政治术语更丰富的语言,充满说服力地阐述意识形态问题。
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只比江青年长十岁。然而,从代际上看,她们之间的差异更大。邓颖超属于第一代共产党员,他们是毛主席的同辈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投身于革命运动。江青则属于第二代革命者,其中一些人在30年代初于国统区与共产党有过接触,但直到30年代末才与毛主席在苏区延安相识。
邓颖超和蔡畅(李富春的妻子,也是一位独当一面的革命家),连同其他一些创始代的女性,她们个人已经从旧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将一生奉献给一项宏大的任务:在政治上唤醒、组织和改造中国的女性。邓颖超明确且毫不回避地将自己首要的责任定位为解决女性特有的问题,并且习惯于在所有政治场合中与女性站在一起,这使她与江青截然不同。江青的女性主义更多是在私下里追求的,而她崇高的政治抱负要求她不能将自己的人生根本上定义为一场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
然而,我并未与江青失去联系。在与邓颖超交谈的接下来的每个下午,徐尔维和申若芸这两位特使都会来到我的房间,继续为我朗读江青的讲话。徐和沈不仅是顶尖的翻译,也不仅仅是政府机构的职员。他们的政治立场坚定,口才出众,同样被视为文化的诠释者。沈若芸迷人的个性、清秀的外貌、卓越的语言能力、敏锐的政治嗅觉以及冷静专业的风范,无论在哪个社会都能保证她的成功。她这些非凡的才能,使她对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严格遵循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尽管这为她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知名度和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在伦敦学习了一年半,随后与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1972年,她陪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首次对美国的破冰外交访问。1972年夏天,她在最敏感的任务中为江青服务。同年晚些时候,她作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私人翻译再次来到美国。1974年,她被提拔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担任职务。
在我与江青意外会面之后,沈女士开始不分昼夜地来找我。除了政治读物外,她还给我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江青和主席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彩色艺术照片、一套瓷熊猫(来自著名的景德镇窑,尽管这种产品自清朝时期以来已经失传)以及江青生平的其他纪念品。在她的艺术照片中,风景和花卉——两者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受欢迎的主题——我很想看到昔日官僚阶层的笔法在技术上的更新。这种在艺术上的多才多艺,加上对园艺的神秘迷恋、对自我疗愈的痴迷、对体能的自豪以及对戏剧的官方赞助,使她从文化的角度与中国的帝国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样,德高望重的毛主席、总司令朱德、浮士德式的郭沫若,以及其他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精神的资深革命家,继续以古典诗词的形式进行创作并发表作品。然而,那些不那么崇高的同志以及在他们之下受教育的后代,却被排除在这一崇高传统之外。如同他们的帝国前辈一样,包括江青在内的当今领导人,无论技艺多么精湛,都不愿自诩为业余爱好者。我饶有兴致地查看她的照片,发现照片背面的题词是用红铅笔书写的,这是皇帝签名常用的朱墨的无产阶级化改良版。
在沈的斡旋下,江青开玩笑地测试了我的摄影技术。在她用种子培育的牡丹肖像照中,她使用的是自然光还是人工照明?照片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拍摄的?大气中的水分来源是什么?我兴致勃勃地向沈提交了我的猜测。第二天,她带着正确的答案回来了,并告诉我江青得知我被她的巧妙技艺误导时有多开心。我猜是早晨阳光下的自然光,而实际上江青在秘书的帮助下,在黄昏时分使用了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工照明系统。我还推测花瓣上晶莹剔透的水珠是自然降水的结果,而实际上她在拍摄前用手指轻轻地将水滴在花瓣上。
8月第三周晚些时候,我的上海之行开始了。这次行程由一个规模扩大的向导团队负责。除了北京的常驻向导外,又增加了五位女性和一名男性,他们都来自上海的艺术、科学和外事管理领域。毫无疑问,这种官方的重视是江青首次介入我访问的结果,这件事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还配了照片。
在上海,我照常接触了那些“革命奇迹”,包括清醒状态下进行子宫手术,并使用针灸麻醉的女性,她们表现得非常愉快。这似乎是神经阻断加上政治催眠的结合,依然显得很神奇。资产阶级自由派教育家蔡元培最小的女儿蔡焌安,低声讲述了她父亲和她自己丰富而又非意识形态化的详细历史。
在这些上海女性人物中,被政权宣传为模范“新女性”的代表是王秀珍。她是一名纺织工人,在35岁左右时,于1969年被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调研了上海的文化领域,那里被认为是江青的“领地”,而姚文元则是这个领域的“地方守护者”。对备受争议的现代作家鲁迅故居的一天访问,以一场文学辩论告终,这场辩论后来又和江青继续展开。与身经百战的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关于18世纪巨著《红楼梦》的讨论,后来也被她接了过去。此外,京剧和芭蕾舞表演,以及对剧团的采访,都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江青领导下摆脱古典芭蕾束缚的舞蹈家们的详尽采访。我们迎着朦胧的夕阳,驱车前往上海低矮的工业建筑群。我的同伴们望着老陈,她竭力保持镇定,兴奋地宣布:“我们获悉,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在那里思考人生和革命。她会再和你们见面一两次。你们最近几天提出的关于她的所有问题,她都会得到解答。明天你们将乘坐从北京派出的飞机前往广州。我们必须强调,这次旅行是秘密的,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你们的人之外,其他人不得知晓。”
我们会不会被带往一个由女性意志主宰的神话王国(或女王国?)呢?我一边默默地问自己,一边努力让自己回归现实。片刻之后,我们都被眼前这趟旅程中浮现的任务表面上的合理性所逗得哈哈大笑,既荒诞又奇妙。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自然发展之下,江青决定展开她的故事,其严肃性不容置疑。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海代表团来到机场送行。余、老陈和我被领到一片空旷的机场,只剩下一架巨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机上唯一的乘客,都是从北京飞来的——宣传界的知名人士常英、翻译沈若芸,以及礼宾部副部长唐隆平,他现在是我们代表团唯一的男性成员——面带微笑地在门口挥手致意。
飞机内部宽敞,设计精良,与中国普通飞机截然不同。我和常英被带到前舱,那里配备了写字台、餐桌、电子设备,还有一张全尺寸的床,床上铺着绣有精美丝绸床单,还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淡粉色和白色枕头。在那里,常英和我独自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作为一名见习记者的经历,之后她移居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她与江青的人生道路首次交叉。作为宣传部长,她态度更为严厉,而我对鲁迅思想多样性的自由欣赏是那样随心所欲,但她却以严格的党的路线来回应,而这条路线只珍视鲁迅共产主义精神的些许闪光。尽管她显然忠于权威,但她的思维也很灵活,我们意识形态上的不合并没有减少相互的尊重或我们处境的舒适。就在我们友好地争论的时候,两个非常漂亮的解放军女孩送来了烤鸭、各种甜食、刚蒸好的包子、精致的水果、冰淇淋、白酒、啤酒和葡萄酒。
喝了中国酒,我放下了戒备,屈服于张颖的渴望,想要在广州未知的旅程到来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她回到了主舱。丝绸床单与清醒时严谨的无产阶级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渐渐失去意识时,一位女乘务员拉开了浅色的窗帘。我一直睡到被副驾驶温柔的声音唤醒,他正俯视着我,用精确的时间和空间数字描述着我们下降到广州三角洲的路线。
“江青同志准备好了!”这句话仿佛在召唤我们离开等候已久的宾馆,驱车前往江青所在的宅邸。黄昏时分,我们的汽车鸣笛穿过广州混乱的车流,人车熙熙攘攘。夜幕降临,我们驶入郊区,颠簸的道路急转弯让人难以辨别方向。通往宅邸的路狭窄蜿蜒,两旁是茂密的竹林。竹林中隐约可见年轻的解放军卫兵,刺刀闪闪发光。这栋宅邸是一栋瘦长的单层现代建筑,坐落在一片静谧的保护区内,周围环绕着热带花园:攀缘的三角梅、鲜艳的木槿花、漂浮在倒映池面上的淡粉色莲花、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鸣声阵阵,鸟儿的歌声不着调。
楼房内部宽敞,但装饰却很平淡,只有几瓶鲜艳的蓝色和金色鸢尾花,以及偶尔出现的卷轴画作点缀其间——全是当代风格,但绝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明确的政治题材。江青远离北方首都,在北方,她饱受官场繁文缛节和个人恩怨的困扰,在这里显得更加柔和放松。她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厚重双绉衬衫式连衣裙,百褶裙垂至小腿中部,这种风格让人想起了我们上世纪50年代初的风格。她依然穿着北京的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包,只是包柄上系着一块破烂不堪的方形毛巾布。“你在我面前紧张吗?你不应该紧张。”
“没有。”事实上,我比第一次见面时轻松多了。我开始做笔记。为了应对酷热潮湿的天气,我把衬衫袖子卷到了肘部以上。
“你太热了,”她观察到后示意助手打开空调,空调吱呀一声启动了,低沉地轰鸣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停了下来。
她回忆起我们大约两周前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周总理问她想不想见我。周总理告诉她,我“年轻,对中国充满热情”,是约翰·S·瑟维斯在与联合国代表团开始谈判后推荐的。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被评价为“中国人民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她当时正准备执行其他任务,却决定留下来与我见面。为什么?否则会显得她傲慢自大。此外,她无法摆脱对中国人民的责任。她也知道我已经见过邓大姐(邓颖超),而且我和邓已经开始了深入的讨论。她匆匆忙忙地安排我去看戏,并告诉我没有时间做精心准备。然后,她苦苦思索该给我什么。想到之前那段焦虑万分、奔波忙碌的日子让她大汗淋漓,她不禁笑了起来。当然,她并不熟悉我,但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她就对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后,她开始更仔细地思考我的工作性质,并确定了一系列采访的“初步构思”(她使用了这个词,但并未解释其确切含义),因为她知道这些采访最终都会被发表。
四五天前,她拂晓便起床,准备飞往广州。为什么是广州?为了暂时告别政府的日常工作,并接受治疗。摆脱了北京的压力,她吃得更好、睡得更好。几天之内,她记忆力——最近几个月断断续续地衰退——就恢复了正常。为了避免我误以为这就是她一贯的消遣方式,她向我保证,她通常会专注于“严肃的政治事务”,并强调道:“我受不了琐事。”我们俩都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琐事上。
在我到达前不久,她向大约一千五百人发表了讲话,并向一群官员报告了当前的情况。除了这些约会之外,她的真正目的是见我,但她强调我们的会面必须保密。如果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群众知道她继续在场,并且与他们关系密切,他们会非常兴奋。如果他们发现她的真正目的是与外国人交谈,他们会感到困惑。因此,除了她、她的随行人员和我的同伴之外,直到八月底离开之前,我都无法与外界联系。
她继续说道,埃德加·斯诺有时间与毛主席、周总理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北工作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性会谈。迄今为止,我交谈过的年龄最大的人是邓颖超。五四运动期间(1919年),她15岁;而江青当时只有5岁,太小了,无法理解那场灾难性的事件。江青承认邓颖超的革命经历比她更长;但她指出,她的革命经历“更广泛”,因为其范围并不局限于妇女事务。
她和其他领导人在西北工作期间(1937-1947年),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她当时的特殊优势(她和毛主席于1938年结婚),她能够比邓颖超更详细地讨论延安时期的情况。虽然她本人没有参加1930年代中期从中央苏区到西北的长征,但她的叙述会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回顾性的信息。她通常专注于她亲身经历的事件。但她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如果我不关心军事,她会略过这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总是“武装到牙齿”,中国人不能没有武器。她坚持认为,中国人不想打仗。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是有区别的。他们从不对别人发动不公正的战争。她放松了眉头,说她无意教条地喋喋不休。
她笑着伸手去拿一个纤细的金丝锦盒,从中取出一把精致的檀香木雕刻小扇。她爱怜地拨弄着,说这扇子她用了很多年。丝绸面的一面手绘着粉色梅花,另一面则镌刻着毛主席的诗《七律·冬云》,作于1962年12月26日,即主席七十岁生日(中国传统的寿星计算方法,以出生日为第一个生日)。诗句如下: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当我略读主席的字迹时,她向我保证,这不是他的真迹。主席的书法堪称艺术品,他的草书闻名遐迩,堪比王羲之。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有机会拥有主席的真迹,他一定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她大手大脚地转过身,向我们展示挂在我们身后墙上的那幅主席书法的大幅复制品,那幅书法粗犷豪放,有时甚至略显飘忽不定。她回到扇子旁,说她已经为我订了一把,很快就会到,不过目前我可以用这把。过了一会儿,她决定把它送给我女儿。“她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德拉。”
她质问道:“你为什么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我说了一些关于俄罗斯人以及其他人的名字是从希腊人那里借来的,尽管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
然后她伸手从桌上的瓷碟中拿起一圈圈白茉莉花和微型白兰花,将手指浸入一碗水中,将水滴泼在花瓣上。这个美丽的仪式开启了未来所有与她共度的夜晚。有时,在谈话的过程中,她会向在场的女士们分发散花。随着风扇在夜里断断续续地飘动几个小时,花香混合着浓郁的檀香,包围了我们,并慢慢地飘散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她热情地问道。我非常好奇她会如何表达,所以我说,作为文化活动主管,她应该保持主动。我知道这和采访一位西方或部分西化的领导人截然不同,他们肯定会问我一系列问题,包括争论。而且,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我意识到,我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兴趣,与她内心深处的人生轨迹以及中国的革命历史,即使不是毫不相关的,也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梦幻般地开始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漫长、痛苦而又浪漫。“但不要只写我,”她急忙补充道。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她建议将自己的人生故事置于整个革命的背景中。当人们考虑到革命经历的全景时,任何一个人的角色都显得非常渺小。而她的角色非常微小,她坚定地说。
我可以自由地与她意见相左,进行辩论;这不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友谊将会长久。她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要曲解她的意思。我回答说:“我无意赞扬或责备她”,希望以此摆脱儒家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教。我的首要目标是准确地传达她所说的话,以及她那种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的个性。她引用鲁迅的话,说她虽然会批评别人,但她总是会更严厉地批评自己。人不可自满。她希望我在中国的独特经历不会让我变得自负。无论一个人的人生多么非凡,都必须保持谦虚。
她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推测我想更多地了解她的个人生活。因此,我们将从战争开始,因为战争原则包含了她所从事的生活以及整个革命动力的线索。如果我不感兴趣,她就不会强迫我讲军事史。然而,她保证,她的演讲不会枯燥乏味。然后,我们将转到个人历史,从童年开始。
那时已是晚上九点。之后她吃了晚饭,并换到另一个房间呼吸新鲜空气,然后一直讲到凌晨三点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的精力也随之增加,她似乎并不介意听众在酷热中因身体迟钝而变得虚弱,甚至昏昏欲睡,而酷热中唯一的活动就是她的独白。
每天晚上,江青都要在警卫员和护士的不断催促下,以及两名私人医生的断断续续的信号下才能结束她的讲述。这两名私人医生要么在房间里踱步,要么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她。除了这些警卫员之外,我们身边通常还有许尔维和沈若芸,她们担任我们的翻译;宣传部副部长常英;礼宾部副部长唐隆平(她政治随行人员中唯一的男性);以及我的两位同伴余世莲和老陈。我和他们偶尔会交换眼神和微笑,不过在江青面前,他们几乎保持着绝对的沉默——与他们平时的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个晚上,我们换到了一个更大的楼房(尽管江青仍住在第一个楼里)。这栋楼有更多的房间,当闷热的南方空气变得沉闷时,我们可以依次使用这些房间。每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都配备了同样的东西:毛巾(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冷的),我们用它们来提神,茶具、香烟、几碗、干果、书写工具、信纸、矮桌上的麦克风、以及其他录音设备。
我们的访谈持续了六天,模式是傍晚开始,然后停下来吃一顿很晚的晚餐,之后继续讨论直到凌晨。有一次,我们还在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各增加了一场访谈。就这样,江青以她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极其严谨的无产阶级作风,向我讲述了她革命生涯的奇妙之旅。
待续……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