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做的这件事,比养他一辈子更伟大

1883年3月17日,伦敦海格特公墓。
春寒料峭,气氛肃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站在挚友卡尔·马克思的墓前,用他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发表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悼词。
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在场的亲友们,无不为这份超越生死的友情感动。他们以为,恩格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用金钱和智慧供养着马克思,已经做到了友情的极致。
但他们不知道,对于恩格斯而言,真正的考验,此刻才刚刚开始。
送别了挚友,这位63岁的老人,将独自一人,扛起比泰山还重的嘱托。他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比“养”马克思一辈子,更艰难,也更伟大。
他要做的,是让马克思,在思想的世界里,“永生”。
01. “魔鬼的手稿”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走进他位于伦敦的书房,心情无比沉重。
书房里,除了满架的藏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堆积如山的、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倾注了半生心血,却未能完成的史诗巨著——《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当恩格斯打开这些手稿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摆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草稿”,而是一片思想的“原始森林”。

首先,是字迹的挑战。马克思的字迹,是出了名的“天书”。潦草、细小,涂改和缩写随处可见,很多单词只有长期与他通信的恩格斯才能勉强辨认。马克思的女儿燕妮曾开玩笑说,如果父亲靠写字为生,早就饿死了。
其次,是内容的混乱。这些手稿,不是按照章节顺序写成的。它们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的思考片段,有些是完整的章节,有些只是一段话,甚至只有一个标题。各种观点、引文、数据、数学公式,像一锅大杂烩,毫无章法地堆砌在一起。
最致命的,是思想的艰深。《资本论》本身就是一座思想的珠穆朗玛峰。而这些手稿,记录的是攀登者在攀爬过程中最崎岖、最原始的思考路径。里面充满了大量的逻辑推演和复杂的数学运算,许多地方,马克思本人都还在探索之中。
面对这堆“魔鬼的手稿”,任何一个学者,恐怕都会选择放弃。整理它,不仅需要超凡的耐心和毅力,更需要与作者本人同等水平的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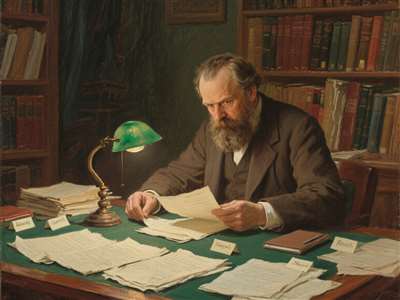
环顾整个世界,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只有一个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他别无选择。他知道,如果他不做,这些凝聚了挚友一生智慧的结晶,将永远埋没在故纸堆里,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遗憾。
这是马克思无声的托付,也是他对挚友最后的责任。
于是,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戴上老花镜,在昏黄的灯光下,坐了下来。
这一坐,就是整整十年。
02. 十年枯坐,只为一次灵魂的对话
整理《资本论》的日子,是恩格斯一生中最孤独、最艰苦的岁月。
他每天的工作,就像一个最严谨的考古学家,在一个庞大的遗迹中,小心翼翼地挖掘、拼接、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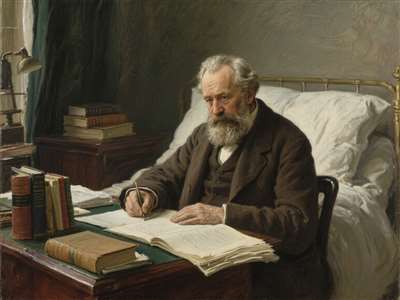
他要把数千页的手稿,一页一页地抄录下来,因为原稿太珍贵,经不起反复翻阅。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辨认每一个“鬼画符”般的单词。遇到实在看不懂的,他就要去翻阅马克思生前的信件、笔记,甚至求助于马克思的女儿,试图从他们的回忆中,找到一丝线索。
抄录完成后,是更艰巨的编辑工作。
他要像一个侦探一样,根据零散的线索,判断哪一段属于哪个章节,哪句话是马克思最终的定论,哪句话又只是一个临时的想法。他要理清整部书的逻辑结构,让那些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完整的项链。
最困难的时候,他常常对着一段话枯坐几个小时,试图进入马克思的大脑,去想象挚友在写下这段话时的真实意图。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编辑整理,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灵魂对话。
他的视力,在这场浩繁的工程中,急剧恶化。医生多次警告他,必须停止工作,否则有失明的危险。
但他没有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必须独自搞完这一切,否则,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部著作的这一部分就永远只是一部残稿。”

除了整理手稿,他还要应付来自全世界的“敌人”和“朋友”。
马克思去世后,许多人开始歪曲、攻击他的学说。恩格斯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奋笔疾书,写下大量的文章和信件,去澄清事实,捍卫挚友的思想阵地。他成了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解释者”和“守护神”。
同时,他还要指导风起云涌的国际工人运动,回复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来信。他在伦敦的家,成了全世界革命者的“总参谋部”。他要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指点迷津,要为法国的工人党调解纠纷,要为俄国的革命者提供建议。
白天,他是运筹帷幄的“将军”;晚上,他变回那个在故纸堆里默默耕耘的“老学究”。
这十年,恩格斯几乎是以一种“燃烧自己”的方式在工作。他牺牲了自己的研究时间,放弃了许多自己想写的著作。他把自己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宝贵的十年,全部奉献给了他已经逝去的朋友。
03. “第二提琴手”的谢幕:他用生命,为一部巨著作了结尾
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94年,在与喉癌的痛苦斗争中,74岁的恩格斯,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当他为这部巨著的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时,他如释重负。
他在第三卷的序言中,谦虚地写道:“我所做的,只是把我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尽可能按照他的精神发表出来。”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绝非“整理”二字可以概括。恩格斯不仅是编辑,更是合作者和阐释者。他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填补了手稿中缺失的环节,澄清了模糊不清的观点,使得这部天书般的著作,最终能以一个完整、清晰、雄辩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没有恩格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将是一部残缺的“断臂维纳斯”。正是恩格斯,为她安上了双臂,让她得以展现出完整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完成了这项使命,恩格斯也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生命。1895年8月5日,他因喉癌在伦敦逝世。
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任何仪式,骨灰装在瓮里,沉入他深爱的大海。
他来时,是莱茵河畔的富家公子,走时,是孑然一身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把万贯家财和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他所信仰的事业和所珍视的友谊。
回顾恩格斯的一生,人们总爱用他自己的比喻,称他为“第二提琴手”。他似乎永远站在马克思的光环之下。
然而,当大幕落下,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位“第二提琴手”,在首席缺席之后,以无与伦比的技艺和无比坚定的忠诚,独自一人,奏完了整部交响乐最华彩、最艰难的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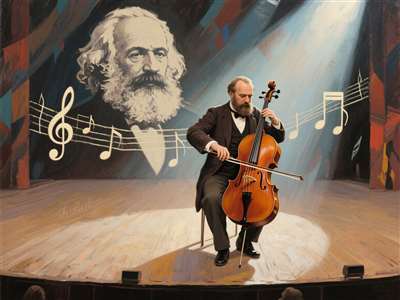
他的伟大,不在于开创,而在于完成;不在于引领,而在于守护。
这种为了理想和友谊,甘愿自我牺牲、默默坚守的品质,在任何时代,都足以让所有光芒四射的天才,黯然失色。
这位一生都在战斗的巨人,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消费主义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读一个19世纪的老头子?他的思想,真的还“管用”吗?
下一篇,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终篇,我们将一起探讨,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