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再次“被迫出山”
遇事要找根源,举一才能反三。就像释永信的问题,只盯他个人骂远远不够,更该追问一下:相关的管理规则是否该完善?曾经的相关调查是否有错误?类似的争议是否早该有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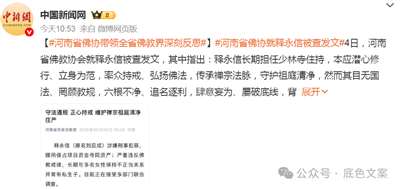
释永信之事,省佛协再发新文痛批。其个人是非,官方为准。
只是这场面,突然叫人想起百年前,也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琦善,且看逻辑像或不像。
1.
鸦片战争开始后,琦善的名字就没干净过。说书人咬牙切齿,讲他是奸贼,跟洋鬼子妥协,丢了大清的脸。
战后《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这些书,把他钉死在“奸臣”柱子上。字里行间,都在说“若非琦善坏事,天朝怎会输?”
可这帽子,真该他戴吗?
说到底,出了事,头一个要保的,是道光帝。
那会儿皇权压顶,天子得是“圣明”的,错不能在皇上。于是有了“奸臣模式”:出了岔子,就说“奸臣欺君”,锅全甩给臣子。
“妥协”是道光帝定的,输了却让琦善扛;若成了,功劳也是皇上圣裁。
尽管当时有人敢影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却没一个人敢在纸上写“道光帝错了”——谁都怕犯了“以下犯上”的忌。
2.
那时候的人,无法接受“天朝输了”。
士大夫们捧着圣贤书,天天说“我朝是天朝上国,蛮夷岂能匹敌?”可洋人的枪炮一响,清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城门都守不住。
这脸怎么搁?
他们不愿承认,问题出在天天吹的“天朝制度”上——不愿承认船不如人、炮不如人,更不愿承认思想不如人。
于是只能找个“靶子”骂:都是琦善的错!是他“剿夷”不力,是他跟洋鬼子讲和!
琦善一个人不够,就拉上浙江的伊里布、江苏的耆英,说他们都是“一伙的奸臣”;又把希望搁在林则徐身上,说“重用林大人就会赢!”
林则徐受捧,从不是因他偷偷学洋人的技术、了解洋人的国情——这些事在当时是“丢人的”,他自己都不敢声张。
只是他摆出“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架势——这才合了“天朝”的面子,合了所有人不愿面对现实的心思。
3.
不能说“忠奸论”全是假的。
毕竟鸦片战争里,有关天培、陈化成战死沙场,也有余步云之流贪生怕死。可这理论的致命伤,是把“复杂的问题”全简化成了“换几个人”。
按这逻辑,中国要赢,只要撤了琦善、重用林则徐就行——不用改船炮,不用改制度,甚至不用改“天朝上国”的想法。
再往深了说,要想让忠臣有出路,奸臣不露头,就得把传统的“纲纪伦常”抓得更紧。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暴露的不是“天朝”的毛病或落后;反倒证明天朝的圣贤书和制度全是对的,坏就坏在那些“奸臣”没照着做。
琦善哪里只是道光帝的替罪羊?他是替整个“天朝旧道统”背了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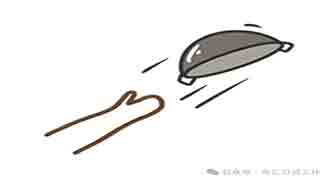
4.
“奸臣模式”不是鸦片战争独有。
它像个“万能模板”,代代相传:遇事不找根源,先抓个“执行者”骂。
企业出问题,先开基层员工,却不优化管理制度;项目搞砸,先怪办事人没用,却不提原计划本就不切实际。
就像释永信的问题,众人只盯他个人骂,不追问:相关的管理规则是否该完善?曾经的相关调查是否有错误?类似的争议是否早该有说法?
琦善的“奸臣”帽子,扣了一百多年。今天我们聊他,不是洗白——他确实有他的糊涂和错。
是想借着这桩旧事问一句:我们真的改了“抓靶子”的习惯吗?我们读历史,难道只是为了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还是说,我们该从过去学会:少一点骂“靶子”的冲动,多一点挖“根子”的耐心?毕竟,历史不缺笑话,没人想走弯路。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