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赛国革命文艺列传(鲁迅篇)
有流量党又拿鲁迅吸烟被投诉作妖了,我们穿透乌烟瘴气的嘈杂,换一个视角来走近鲁迅、了解鲁迅。
前言
许多同志希望有进步的文艺欣赏和创作的需求,但可能苦于自己是“外行”,或者受当今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观念干扰过多,不知道从何开始学习研究。因此,一个从当下的眼光去试着讲评赛国现当代革命文艺创作者们探索得失的系列文章由此而来。它将在大体上按时间顺序,从革命文艺的角度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文艺工作者或团体,讲解与批判他们的文艺思想、创作内容和创作方法。这个系列将以通俗易懂、重点突出和联系现实为三大追求,让读者同志们一方面可以据此了解对应作家的主要创作内容及其相关文艺思想的得失,形成较为清晰的认知;又能以其探索实践为参考,举一反三,批判扬弃,于当下更为自觉而有效地展开革命的文艺赏析和文艺创作的探索实践。
鲁迅篇
一、赛国现代文学与革命文艺的先驱
鲁迅是赛国现代文学(也就是白话文的文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不但为赛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 三大文学类别的开端都做出了极大的实际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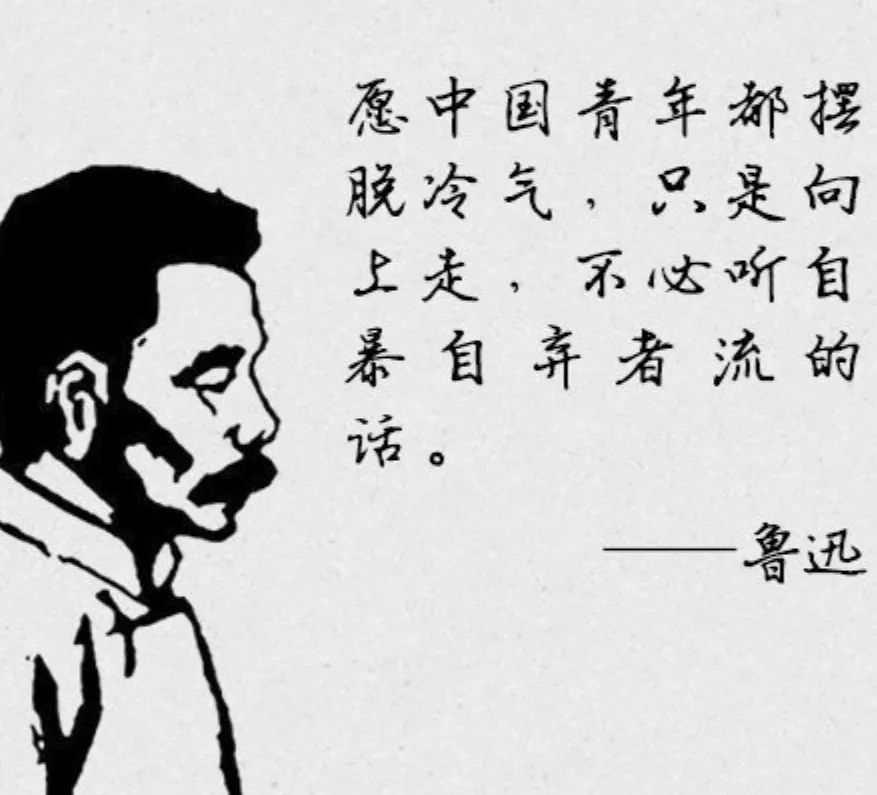
1.现实主义方面的经典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后续充满现实批判的战斗性的杂文,这是鲁迅的主战场,其具有批判现实的强烈斗志,我们在后文会重点展开探讨这部分内容的发展流变;
2.现代主义方面,鲁迅为赛国带来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运用了许多心理学以及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后来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也是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多意性。;(此处受篇幅限制不再展开解析,如果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看钱理群的《鲁迅作品细读》《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这两部小书。)甚至在他的一些杂文里,也可能出现一些天马行空的奇特文笔,如《论辩的魂灵》一文,只是将反对改革的迂腐无赖之辞精挑细选,拼贴陈列,如同百年之后的“鉴定网络热门生物视频”,最终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3.浪漫主义方面,早在距文学革命发生尚有十年的1907年,鲁迅便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称赞了“摩罗诗人”(mara的音译,即被反对者斥为“魔鬼诗人”者)拜伦、雪莱、裴多斐等浪漫主义诗人,称赞他们的诗篇和其中的思想是可以打破陈腐的旧制,为民族国家唤来强力的新生。他赞扬这些发出对旧制序充满反抗与挑战声音的摩罗诗人,认为他们是文学上的战斗者,是民族焕发新生的希望。这种文学思想很长一段时期都对鲁迅的创作有着较大影响,后文还会讲到。
而对于赛国革命文艺的探索,鲁迅也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先驱者的作用:
在赛国革命文学或者说左翼文学方面,鲁迅的探索同样是我们讨论的起点。他是赛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对于国民思想性格的剖析,对于革命的战斗性文艺思想方面的探索、相关技巧手法的运用,尤其是在杂文也就是如今的新闻时评方面所达到的通俗、简洁、深刻,都是我们所急需的。总之,在深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荼毒的“资产阶级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拾源自鲁迅的革命的战斗的新文艺。
二、鲁迅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里需要指出:鲁迅的思想绝非生来就完成了进步,它是有着一个类似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发展转化过程,不加区别的全盘接纳,就无法对鲁迅的革命的文艺思想形成深刻的了解,而且往往还要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蒙骗。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并把这类“马克思主义”奉为真理,读者们应该很熟悉这类阴险的套路。反动文人们也时常把鲁迅的前期尤其是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大加赞扬,而对后期的战斗锋芒更强的战斗性杂文闭口不谈;再或者有的对于鲁迅作品胡乱归类,如鲁迅所讽刺的“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更有最为反动者,拿着鲁迅早期的创作思想洋洋得意,声称鲁迅此人绝对跟不上新赛国的wg。这种抹杀鲁迅思想革命性的歹毒评论,于当下并不少见。
因此,关于鲁迅思想的分析评价我们必须有所区分,其中不怀好意的混淆还要加以警惕。而做到这一步的前提,就是先来简单梳理一下鲁迅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
鲁迅早期的创作是很受进化论、尼采的思想以及“摩罗诗人”拜伦的英雄主义之类的影响,较单纯的认为历史的潮流是新的战胜旧的,国家的希望与新生在于“先驱者”去启蒙代表新事物的青年或者“救救孩子”,最终可以“任个人而排众数”,也就是类似尼采所设想的那样推翻了奴隶的道德,实现了个人价值的觉醒。然而他的这些理论基础对于社会尚未有系统深刻的认识,批判对抗虽猛烈,然而缺少切实有效的方案作为根据,于是只得停留在麻木的“国民性”或者看客精神之类的发掘,看不到他所批判的闰土、阿Q或祥林嫂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他弃医从文的宏愿在其创作早期如辛亥革命本身一样,轰轰烈烈地走向必然的失败。
不久,现实社会的复杂困难,诸如军阀混战和4.12反革命政变之类让他的“呐喊”变成了“彷徨”,这使他的怀疑与批判也逐渐接近虚无主义了。《故事新编•铸剑》有类似的战斗的和复仇的描写,虽然终于复仇成功了,然而统治者与反抗者的头颅在锅里烂作一团,甚至还要和暴君一同下葬成为“三王墓”,而围观的平民们依然只是蒙昧地喧嚷围观。这种带有绝望和虚无意味的结局很能体现他此时的低落心态。而他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在坚持着战斗,而战斗的意义就变成了他对许广平所讲的:“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这种看不到希望的个人主义式反抗以及虚无主义的结局在散文诗《野草》里亦多有体现,他甚至要把这绝望当作自己继续革命下去的动力。如在《墓碣文》自称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再比如《这样的战士》,主角虽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然而却势单力薄,终于孤独的倒在无物之阵里,然而结尾却仍然强调“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种虚无与迷茫一直持续到1930年前后,这位在困境中坚持的文学战士在他《三闲集》与《二心集》的创作阶段迎来了新的革命性转变。这一时期共产党创立了赛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成为了其中的旗帜人物,他也已经逐在这个时段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让他文章的批判与战斗性更加地强烈而精准。鲁迅后续的杂文虽然依旧是他擅长的社会批判领域,然而创作的动机与主题已经集中在了反帝反封建,揭露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昏暗统治,以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点古今中外事物,警示今人。前者如在《二心集•智识劳动者万岁》一文,讽刺无耻的反动统治者造词“智识劳动者”以自居,实际上是混淆阶级立场,是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为了自保而让饱受压迫的真正的劳动者去受骗送死的丑恶嘴脸;后者如在《南腔北调集》中,鲁迅从《经验》《谚语》之类的小事考据,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各类谚语俗话背后的阶级性,深刻的指出“各人自扫门前雪”是在劝被压迫者不要管闲事,只许服从,而压迫者却总能滥用职权,不受限制。如此种种,皆可看到鲁迅文艺中的新的革命锋芒愈发显露。
最后,我们来看看《三闲集•序言》中鲁迅的自述,以便对上述的思想流变分析有一个大致的印证——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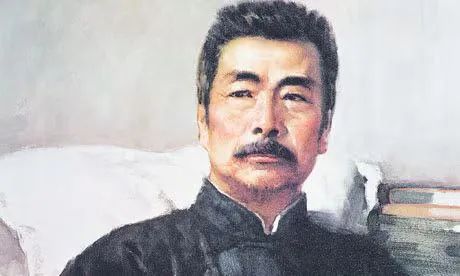
三、鲁迅战斗式创作技巧的学习
这位文坛的战士在他的杂文或通信中较为松散的留下过很多创作题材选取和技巧方面的分享,从他本身的许多小说、记叙文或者杂文时评中,我们同样可以提炼出许多有用的写作技巧:
1.批判与否定,用唯物辩证法让文章走向战斗与深刻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卡尔马克思
因着革命作家的觉悟与操守,鲁迅在辩证法的运用方面有点“天生”的意味了,或者说他对人对己,对任何阶级的批判、解剖与怀疑都是不留情面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因而,他的文章总是自发的或自觉的带着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色彩。这让他在写人记叙或者时评杂谈时,不仅富有战斗性,而且都带有常人所不曾达到的全面与深刻。

如《故乡》一文,虽在重点刻画“闰土”的麻木形象,然而在小说结尾,批判的刀锋却一转他自身--“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 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这里思想的跳跃虽大,但却自然顺畅,他没有因为自身知识分子的身份就要居高临下,也不会因为看到农民更落后就对他自身的局限性选择避而不谈,正是这种无情的批判与否定,他才能真正深刻而全面的展示出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
在杂文中,鲁迅写作的批判与辩证色彩同样非常浓厚。鲁迅经常用一个词“然而”或“但是”,这几乎要成他的思维习惯。比如下文这段,他质疑左翼文学是否在真正地发展壮大,用着马列主义的新的分析依据--“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是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诸如此类于事物发展过程中于肯定中包含否定的理解,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无情解析与批判,是鲁迅可以始终坚持深刻与战斗性的重要前提。他最终走向马列主义,有着他思维习惯的必然性。
鲁迅能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创作品质就是这一革命性与批判性思维,倘若用比较诗意的话总结此类创作习惯,那么《野草•求乞者》里的句子可以来概述——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少些麻木与享乐,多些鲁迅想要赠予的“烦腻、疑心与憎恶”,如此,我们或可同样为思想留存更多的批判性与战斗性。
2.战斗的文艺离不开进步的立场和真实的生活:
文章想要拥有战斗性,就必须是作家在进步立场下所体验到的现实生活。鲁迅的锋利无情的笔触建立在真实可感的现实生活中。不论是议论还是抒情,倘若不是自身亲自经历,只是赶时髦或者政治正确才写,那就容易堕入虚伪;倘若苟安现状,在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忘却战斗性,自身思想长年累月拒绝变革,就会被时代抛弃。鲁迅本人就是战斗性文艺的坚定创作者:鲁迅本人在题材方面,从小说到杂文为主的转变,亦是出于文学的战斗性考虑而做出的抉择。尽管鲁迅在小说方面创作的逐渐停止对于一些饱食终日的“批评家”们来说是“可惜的事”,然而这个选择对于鲁迅这一位文学界的战士来说却又有些必然的意味--因为他更重视杂文的即时而直接的批判性与战斗性。
关于战斗文艺的创作鲁迅与人讨论很多:
艾芜、沙汀跟鲁迅写信说自己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想写出有时代意义的文学,因此决定把题材放在剖析小资青年和记录底层民众的挣扎方面,问鲁迅此种方向可不可行。
鲁迅对此没有简单的回答行还是不行,他首先支持两位青年的创作想法,认为只要写自己熟悉经历的生活,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们提的这两种创作内容都可以为时代做出战斗性的贡献。但同时毫不避讳的指出了小资写底层生活的“客观”可能就像酒楼上的冷眼旁观,如果不逐渐改革自身的落后思想,只想“保卫我的现代生活”,不愿真正的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那么就可能变成空虚的布施,甚至让一个安于小资身份的作家落后到将来反动的地步。(《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文学创作能否保持一种战斗性,于当时和现在最重要的是作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表现或审视他的生活和见闻。鲁迅在这方面几乎达到了”一花一叶皆可伤人”的境界,他不但在日常生活和新闻评价中表现出战斗性,在一些近似学术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其议论推测同样有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战斗性,如在讨论民间戏剧的脸谱颜色和人物性格的关联动机为何时,他毫不留情地推得结论:“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这段论述不但借助脸谱研究去抨击着“富人”的奸诈,而且无情讽刺了自称中立的“第三种人”(在当时文学界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自称回避政治者)的虚伪与反动本质。
战斗性的另一个前提则是真实性: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是鲁迅后期较为少见的记叙文,他在其中坚持着自已说过的“真实性”原则:鲁迅回忆他与白莽或柔石的接触并无多少轰轰烈烈,反而充满了各种朴实寻常的局促和尴尬:这些充满活力却又带些羞涩的青年时常是忙着做文学社或者探讨一些进步文学的可能,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各种碰钉子甚至坐牢;或者是刚出狱身无分文,只好在热天穿着棉袍找鲁迅讨要稿费,尴尬地相视而笑;再或者一个克服社恐的青年却又好心过头,和鲁迅并排走路时挤得双方都惶恐不安;以及最后给鲁迅留下的狱中报平安的简短书信。以上种种,皆是平常的人生,然而后续写到当鲁迅得知他们的死讯以及后续的悼念时,其于平凡中传达出的痛苦与继续战斗的决心亦是十分地震撼人心。究其原因,也无外乎其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由此可见真实生活带来的真情实感于文学有多大的帮助,而此类战斗性的文学,也必须是作者拥有战斗性的人生方能体察并创作。
关于文学保持战斗性的必要,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也有论述:他分析小品文发展起伏的历史,其中有过“讽刺、攻击、破坏”的战斗时期,也有过被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压制的“小摆设”时期。而今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小品文曾再度充满着挣扎与生存的战斗性,本应当是继续助力于文学革命甚至思想革命的,然而却摇身一变,被一些自甘堕落的文人变成了供人观赏的“幽默”小摆件。鲁迅坚信“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他认为“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发热)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总而言之,所谓生存之文艺,则必须是进步立场下的真实的战斗之文艺。
3.通俗而巧妙的战斗策略
鲁迅在当时同我们一样,要同威不可测的狗审核斗智斗勇,为了应对国统区官方的检查封禁,他的文章往往偏于讽刺幽默,看似通俗寻常,而将革命的锋芒敛藏其中。这在我们如今依然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宣传方式必然要适应在多种情况下进行,因此,时常看看鲁迅后期(1930)之后的杂文,大有帮助。
鲁迅的战斗性文艺创作在“规避审核”方面经验丰富,他不仅经常更换笔名或者找人代发投稿,而且往往将革命的理论润物无声的融入文章。鲁迅极少直接引用理论,有时甚至通篇不谈时政,如在《伪自由书•现代史》一文,通篇在讲变戏法艺人的骗钱手段,讲他们如何换着法子骗取围观群众的钱财,只在最后结尾时“惊叹”自己“跑题”了,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察觉到近代中国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的轮换,不过是变戏法一般对台下的民众巧立名目、巧取豪夺。
这类技巧在如今的许多网友依然在自发的使用了,而它的潜能必然还能更大,有志于互联网的战斗性文艺创作的同志,从鲁迅的杂文,从互联网的网友投稿里,必然可以学到更多的战斗性文艺创作与发表技巧。
以上列举的创作技巧是相辅相成的,有相当多的鲁迅的杂文,便是这样在真实的前提下,运用了马列主义,佐以巧妙的文艺战斗策略,因而即使是学术研究或者幽默杂谈,最终也变为了如投枪匕首一般锋利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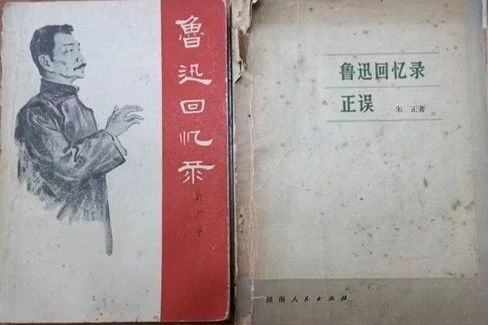
此篇文艺解析仓促而成,希望可以为读者同志们带来关于鲁迅的些许新鲜认识。愿我们都可以如鲁迅那样拿起批判的武器,在对敌人对战友对自身的深刻批判里,在永不止息的战斗人生里,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必可一同迎来铁屋外的黎明。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