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人的尽头是毕业?——别把弱势群体当弱智
之前有个朋友和我讲说,毕业工作之后慢慢觉得学校里常谈的左翼内容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这不是个案,几年前大家就爱开玩笑说“左人的尽头是读博”、“左人的尽头是毕业”、“左人的尽头是婚育”、“左人真成了工人阶级就不会做左人了”……这些话有几分玩笑,几分无奈,其实大家都说不好。

所以,毕业是左人的坟墓吗?我不知道,但如果这话是真的,吴岭大概平均每周都要起尸2-3次。吴岭是大我几岁的一位朋友。身为一个在长三角读大学的东北人,他毕业后又去了珠三角。工作这么多年,感觉他还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好像比学校里头更充沛了。我知道,要给“毕业是左人坟墓吗?”这个问题一个理论分析与回答并不难,但是对于陷在里头的人来讲,怎么从坟墓里头出来呢?
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死灵法师。我只能帮大家问问有能耐起尸的人。以下是吴岭的讲述。
在南方生活,什么感受?
这个得看你先前的“生活史”。
假如你是从农业人口多的市县来珠三角,那在主观感受上,就是“我到了一个更现代的地方”——各种资源堆积,人口基数超大,什么活计都能找到买主,生存手段肯定比老家多。但与此同时,你可能会觉得,似乎这里也没有父辈说的那样“来钱很快”。40多年过去了,外贸红利、人口红利用完了,自由竞争趋近饱和,越来越多流程、规范、审核像补课一样扑过来……往前推十几年,你刚到珠三角,租住在一个城中村,骑着电鸡上马路,上班也不交社保,每天去的商店根本不知消防检疫……没那么多规矩。当然,规矩多也是一种老家没有的“现代化”,接受它的规训,也接受它的福祉。
假如你是从工业人口多的城镇来珠三角,体感可能就不大一样,会觉得穿越回了小时候老家的样子——从所谓“早期现代性”转向“晚期现代性”。早先快速发展没人在意的缺点,现在都被拿到放大镜下,比如城市风貌粗犷啦、精神文化匮乏啦……
早先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捷径,现在人们碰都不敢碰,都怕替别人担保不合规范的风险,比如借名办事啦,赊账垫资啦,容缺批证啦……不是说有人权力寻租,而是人们无意间对“规范体系”有一种非理性的期待,觉得规矩足够多了,就能走出困境。广东人以前是不兴读书入仕的,这几年也都是补偿式育儿,不多生、卷教育、猛考公,“经理文化”逐步盖过“老板文化”,技术人才被后起的政策特区杭州湾挖走,跟90年代的东北一个样。
当然啦,这些没有什么不好;看似日新月异的局面往往是盲从已知的套路,烈火烹油之后的迷茫才会想真创新,人们的心智只有穿越周期才会成长起来。
毕业到了大城市,怎么立足?
毕业换城市是很冒险的,积累那么多人脉不用,去新环境重建社交圈,我到今天也不敢说一点不后悔。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一方面是珠三角应届生工资比长三角高(大学生相对不算过剩),一方面是我有机会持有两地人脉(假如能力强的话,假如)。
当然,前提是职业一定要选好!我毕业前一年择业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个“四不两值”的准则:
● 易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的岗位,不报——没有群众自我治理,你从外部执法或治安,很难处置得当;无群众支持,精神上也吃不消。或者帮大资本回老家打理资源,一旦跟老乡起冲突,性命都容易报销。
● 几乎丧失业余时间的岗位,不报——没时间学习、交际、整活儿,等于社会性冻结。
● 同届学生跟风哄抢的岗位,不报——“信息差红利”殆尽,要请做题家拿身心极限接盘,给岗位的超额利润找依据;从私企到体制,这种位置往往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没有根基的人,真去成了也会高开低走。
● 劳动组织高度个体化的岗位,不报——就让你一个人闷头做事,看不见产业的来龙去脉,不结交同业的朋友人才,不积累上身的能力资源;把“i人岗”作为人生第一份工作,离开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只能给老板留下一眼螺丝孔。
● 当地或业内群众活跃的岗位,值得报——真的能从群众身上学到很多脑子里没装的东西。
● 视野好的岗位,值得报——第一份工作不要图“钱多事少”,生活方式决定咱需要多少钱、多少事,而不是机械地搂钱儿、躲事儿。如何搭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关键靠视野。校招应届生身份,是体验大单位大平台的捷径,什么都有可能见识到,无论当时是好是坏,作为长远规划的数据,都是财富。
我最后找的工作,就是有一些“甲方”色彩,除了和本专业的同事工友服务下游,更多时间要对接服务我们的上游。为了帮乙方疏通堵点、抢出业绩,要找上级争取特办,要找衙门争取快批,早上穿西服汇报吹牛,下午踩工靴调解纠纷……三教九流、商政民学,很多是被迫打交道,当然更多是自己主动熟识,每次稍微多聊两句,拉近关系。在甲方的位置上,学习机会更多,供应方为了证明自己、换取信任,愿意更耐心地披露信息、回答疑问;关键你还可以多方比较、甄别。支撑他们的产业大军什么样,你也能有高位视野望过去,是吧,你提出走访调研,人家可能叫来更多才俊,有问必答。有时候你给他提出要求,人家解释:“我干不了这么多、那么快,是因为某个环节如何如何……除非怎样怎样……”你就更懂他们的组织逻辑了。
如果毕业就做乙方,容易陷入自己的节奏和片面的世界观,社交和信息也会变窄,内耗也多。不过咱们都明白,大部分就业肯定还是乙方岗,乙方收入上限也比甲方高嘛,讨生活永远是硬杠杠。所以我想法是啥呢,有幸做甲方的人,咱要担起责任,把多行业乙方的人才串联起来,大家互通有无。等将来他们有谁去干甲方了,就推广这个方法;等我哪天日子紧巴了,就经他们介绍转去乙方卖气力;这不挺好嘛。
你现在都忙点啥?
头两年主要是“拜码头”。就主动去问长辈亲友、老师同学在华南有无朋友,然后拜访一面。虽然大部分也没深交,但我还是坚持给他们编个名单,逢年过节发点问候,刷个存在感,将来啥事没准能帮一把。改开初期支援珠三角建设,东北各企事业单位来了一大批人,老乡不少,他们再把后生才俊介绍给我认识;甚至还有介绍对象的,那代表人家的信任。另外就是转转社会服务机构,以前珠三角以盛产此物著称,现在潮起潮落、归于平凡。也是好事,大家都更全面地盘点,自己到底几分实力、几分运势,生存未必能给人答案,但至少能检验问题。
个人发展方面,延续上学时候的习惯,四处投稿,给公益活动打零工。我也没能力经营自媒体或者机构,但还是每季度写点东西,投放到我认可的各色账号,总有一家会收稿。这样好,写作范式不会同质化,没有舒适区。另外,我发现一个捷径:通过考证书来学习知识,性价比远高于读研究生。法律、财会、技工,乃至体育艺术,花不了几个钱,考下来还抵税,几千块哩!从毕业到婚育、赡老没几年窗口,趁着还有整块时间,攻克一些技能,将来都有用。
人际关系方面呢,搞点波兰尼说的那种,不那么屈从市场规律的“社会”?我能有什么好招儿?尝试搞一个小社群吧,大多是外省市年轻人,都是各种渠道慢慢认识的。现阶段就是互通有无,介绍自己的行业、故乡,暂时回应大家的信息饥渴吧。以前珠三角社会是各路豪杰“跑马圈地”。基于地缘、血缘形成的圈子包揽某个行业,相互之间秋毫无犯。但近几年各行各业在自己的领地都找不到吃食了,全局萧条倒逼大伙走出藩篱、跨界流动。长远来看,社群慢慢开展一些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复盘,思考自己和家乡的未来,有没有可能用已经积累的职业资源,做一些避免依附式发展的项目、实体?另外,社群一定要注重培养成员自己再孵化社群的能力,不要期待一个社群超过三五十人,而要鼓励大伙按自己的思路再独立孵化,慢慢形成一个“星系”。
走上社会之后,心态有啥变化?
就业几年后,生活和想问题的方式都变了不少。
首先是甩掉了学生时代套在脑袋上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儒家士人文化”意识形态紧箍咒。我现在不是超然的旁观者、评判者了,而是有给定的社会生态位、置身事内了,和各阶层劳动者沟通,都有了符合常识的情景,说笑、斥骂、互助……不必再去刻意反思“我和他者的交往”而维护一种虚幻的道德。前面说的“甲乙方模型”,也暂时解决了一个思想痛点:很多工程师、经理人阶层的左友,心里就遭罪呀,说我到底算不算工人阶级的一员呐?——不算,别纠结啦,基本的唯物主义,你还是得认。但“你不是”不等于“你没用”。人本主义教育从小训练我们追问“我能是什么人?”,其实只要把问题换成“我能有什么用?”,大部分精神内耗就治好了。工人阶级是领导——你不要老惦记挤进领导那桌,要好好想想如何为领导服务!领导想要建立统领、制衡其它群体的能力,需要资源、信息、人脉,要对外发包各种业务,你能不能接得住?甲方问你这样做合不合法,那件事怎么记账,单位怎么管理,社区如何治理,你能不能答明白?甲方叫你找个人物、取送东西、做个玩意,你别给整岔劈喽!乙方服务好,甲方成长快,订单大大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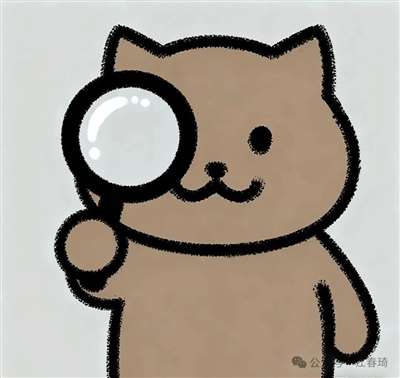
不要沉伦于安逸或浑噩
再者,我觉得上班后更容易筛选议题: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什么即便没用也要保持介入?在学生时代,你看到四面八方的非正义事件,一时间分不清轻重缓急,啥事都想去照量几下。就好像坐在地上望夜空,北斗七星似乎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七兄弟相去甚远,你如果转到侧面看,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我们现在能够望见的问题,和我们短期能够触达的问题,那差老鼻子数量级了。毕业工作以后,你就有了一种能力,可以在一大堆烂事当中筛选出,哪些是群众能忍的,哪些是可能起变化的。许多失权者的工具箱里,根本没有你的位置;许多阵地虽然看得着,但根本没有你的战壕。这种时候还需尊重实际,扮演好一个小参数,间接影响大函数。比如你是工程师,那就先团结你最常交往的技术工,技术工将来去拉拢普工、零工;而不是直接跳去和“最弱势者”搞“连结”,弱势又不是弱智,怎会轻信陌生人?但是话说回来,“有用”不是评价工作的唯一标准。很多事情咱去了肯定是高阶无穷小,发声也是白噪音,但有人保持在场(前提是不作死),仍有战略意义。因为支撑那个事情的高阶力量,可能有一天被其它高阶力量所改变,而那块变化量的数量级,也许就不大了,咱就有活儿干了。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能管两件近切的事,盯两件遐远的事,所有人交叉分工。
另外,毕业后尽早建立“事权思维”和“法人站位”,我也晃了几年才悟出来。大部分人口受的教育训练,都是要先“请出”一个大前提,然后演绎得到结果,最后接受标准答案的评判;理科文科都是这样训练。因为过去40年社会需要大批量能承接产业转移的人口,不需要什么原始创新,归纳法不如演绎法重要。但现在社会需要解决前所未有的问题,受到这种教育人就对创新之前的合法性“授权”有某种肌肉性依赖——要先正名,要去污名,要被看见,要被接纳,要统一思想,要取得大多数同意——如此这般才能开始干活儿,心里才踏实。这是什么踏实呢?是鸡同鸭讲疲于自证的踏实,是在鬣狗秃鹫面前“被看见”的踏实。上班以后才明白,做哪些说哪些在一线经办人把控,有实利实害了才能配套评价,“授权”是对“事权”的追认,规则是对实事的言说,而从来不是先导。能把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关联到一次革新的进程中,唠唠叨叨乞求认同的就是你的对手了。“法人站位”是我工作后另一个收获,今天的社会其实很难信任某个自然人了,工作预见的人尊重我,是冲着我么?不,是冲着我背后的法人团体,我是借大树乘凉。我认为自然人无法穿越团体/群体这个中介变量,而直接干预社会结构,人多势众也白搭。你看2016年以来全球民粹右翼办成一件改革了么?还不是给大财团耍活宝。现在互联网上的个人,看起来都像信号收发元器件,仿佛社会要完犊子了。
其实什么都没改变,顶多是启蒙主义半身入土了而已,真正的利益、长期的选择都存储在法人人格中,譬如单位、社区、会社等等领域。一群合拍的人,均以自然人的名义,只能走访调研,讲讲故事。但假如你们依托一个法人,就能看到崭新的世界向你展开,可以践行外部缔约、内部民主、厘清公私、培养后进、访贤达、跑衙门、拆并、腾挪……如果还能进一步,多个法人形成互助网络,那就完全迈入新境界了。
最后,上班让身心更加健康了。作息变规律,到点就领钱,20多年来再次体会晚上没作业的快乐。工作再忙,也都是帮别人办事,没有真正指向自己的事,手虽忙,心不慌,脸皮加厚,顿感增强;不像考试、论文这些冤家,整不好钻牛角尖出人命啊。同时,因大量时间浪费在雇佣劳动中,所以更珍惜业余时间,办事效率更高。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