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同?
这面在一百多年前由列宁高高举起的、染红了十月革命炮火、饱经风霜的旗帜,是 指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一面永不磨灭的旗帜。
引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回望与前瞻
在人类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列宁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的注脚,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重大历史转折。它不再是沉湎于学院书斋的理论探讨,而是震耳欲聋的十月革命的划时代炮声;它不再是百年前《共产党宣言》中那句震撼人心的预言——“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而是真正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广袤土地上,首次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幽灵化为现实的铁证。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一天起,它就从未停止过被其敌人所恶意歪曲与疯狂攻击,甚至被那些打着“同志”旗号的“朋友”所阉割与背叛。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锋利的革命刃锋,自然也始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和一切革命叛徒们集中围剿的火力焦点。
他们惯用的伎俩,不外乎几类:或将其诋毁为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变种”,一种充满“东方专制色彩”的异类;或将其狭隘地理解为一套僵化、“过时了的”俄国特定战术手册;更有甚者,玩弄着“褒马贬列”的伪善把戏,试图将马克思描绘成一位超脱世俗、只谈人道的“理想主义学者”,而将列宁贬低为一位“冷酷无情”的“权谋家”——其根本目的,就是粗暴地割裂理论与实践、割裂革命导师与革命领袖之间那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链条。
那么,什么是列宁主义?
本文的写作使命,正是要彻底撕碎这些经年累月的谎言与迷雾,迫使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革命源头,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最高点,系统地回答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将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证明:列宁主义绝非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种“偏差”或“变异”,它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步入帝国主义和全球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所必然发生的、唯一科学的、活生生的、战斗形态的继承、捍卫与伟大发展。它不是一套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从“仅仅批判世界”向“彻底改造世界”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实践纲领。
第一章:新时代的呼唤——帝国主义:列宁主义不可回避的历史前提
1.1历史的转折: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霸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的导师所身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尚处于“自由竞争”的青春期。他们那不朽的理论功绩,在于穿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重迷雾,深刻揭示了其基本矛盾、剩余价值的惊天秘密,以及其无可避免地将被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所取代的历史总趋势。毫无疑问,他们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事业,奠立了坚如磐石的科学理论基石。
然而,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历史的步伐从未停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身却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质的蜕变。无情的自由竞争加速了生产的极端集中,最终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垄断的巨头。资本主义,如同一个从“青年”迈向“暮年”的生命体,进入了其最高、同时也是其最后的、腐朽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这是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不及完整亲身经历,也未能为之详细解答的崭新历史局面。面对新的时代难题,科学的革命理论,就必须给出新的、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重任,无可逃避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
1.2理论的穿透力: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与“垂死”的本质
列宁在他那部洞察历史、熠熠生辉的理论巨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以其无与伦比的理论穿透力与细致入微的经济分析,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解剖。他超越了纯粹的描述,科学地、精炼地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五大核心经济特征:
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垄断组织的绝对统治。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势力滔天的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垄断一切的金融寡头。
资本输出(而非传统的商品输出)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形成的国际垄断资本同盟横空出世。
世界领土已被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彻底瓜分完毕,矛盾和冲突积累至极点。
正是基于对这五大特征的深刻把握,列宁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结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因为垄断和金融霸权的全面建立,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如同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顶点。
1.3“薄弱环节”的战略思考:对历史辩证法的精确运用
这一深刻的帝国主义分析,并非纯粹的学术探讨,它直接构成了列宁主义最核心的战略基石之一: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的伟大构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当时的形势,曾设想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几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或相继爆发。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情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敏锐地捕捉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这个全球性的链条其强度是极不均衡的。因此,革命的爆发,将不再必然地首发于那些最强、最成熟的国家,反而最有可能在那个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即矛盾最尖锐、统治阶级最腐朽无能的国家——率先冲破束缚,取得胜利。
这个被历史选中的“薄弱环节”,正是当时沙皇俄国。因此,列宁主义,首先就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如何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薄弱环节”上,精确地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科学。这种基于新的世界格局所作出的战略调整与理论创新,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理,在新的、不平衡的全球格局中,所进行的一次最精确、最富于创造性的运用。
第二章:革命的总参谋部——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学说
2.1批判“自发论”的惰性:工联主义的局限性
列宁主义的第二个、也是在组织形态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巨大贡献,集中体现在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这部学说最精髓的表达,正是那部充满战斗檄文风格的著作《怎么办?》
列宁将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主义”和“自发论”。他以不妥协的理论勇气深刻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仅仅依靠其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例如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的罢工等),其所能产生的最高意识,至多只是“工会意识”(即“工联主义”),绝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要求彻底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
2.2理论的“灌输”:革命意识的来源与使命
那么,科学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意识,究竟从何而来?列宁对此给出了斩钉截铁的、毫不含糊的回答:它“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革命意识,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由那些最坚定的、具有高度理论修养的革命知识分子(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系统总结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遗产和所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
因此,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的历史任务,就在于充当革命理论与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坚固桥梁。它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灌输”到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头脑与心灵之中,将他们从自在的、如同散沙般的分散状态,转变为自为的、有组织、有目标的革命阶级。
2.3“职业革命家”的熔炉:先锋队的组织重塑
为了能够承担并完成这一异常艰巨、充满风险的革命使命,这个党,决不能是第二国际那种松散的、允许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混杂泛滥的“清谈俱乐部”。它必须是一种“党的新的组织形式”,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列宁明确要求,这个先锋队,必须由那些对共产主义事业最忠诚、意志最坚定,并视革命为自己唯一神圣事业的**“职业革命家”所构成。它必须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纪律严明、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组织。它不是普通的政治团体,它如同一个高度协调、随时待命的“革命总参谋部”**,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
2.4民主集中制:党的生命组织原则
正是为了实现先锋队的高度统一和战斗力,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伟大的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是列宁主义对组织理论的独特发展。
民主,首先体现在党内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广泛的民主,允许公开的、同志式的思想争鸣、讨论和批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由选举产生,并对全体党员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集中,则体现在一旦党的决议通过并形成,全党的所有成员就必须以铁一般的纪律无条件地执行。
这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原则体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只有这种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中,才能确保党在残酷的地下斗争和公开的夺权战斗中,始终保持思想的统一、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使其成为一把无坚不摧、足以砸碎旧国家机器的革命利剑。
第三章:革命的核心问题——“打碎”旧国家机器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3.1抢救“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革命灵魂
列宁主义的第三个核心贡献,是其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这部学说被精辟地浓缩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之中。
在列宁之前,第二国际的那些修正主义领袖们(以考茨基、伯恩施坦为代表),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和“渐进改良”的幻想,早已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最核心、最激进的革命灵魂,彻底地背叛和抛弃。他们公然鼓吹,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票,从而“和平地”、“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无需进行暴力革命,更无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列宁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从故纸堆中,重新发掘了这部分“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他系统性地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得出的最根本、最具颠覆性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将其彻底地打碎、摧毁。
3.2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国家的阶级本质
列宁深刻地、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一种由“特殊的武装队伍”(包括常备军、警察、法庭、监狱等)所构成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其外表多么“完善”、“自由”,其本质始终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
因此,指望这个专为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而精心设计的暴力机器,会“和平地”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政治上的天真,更是理论上的最致命幻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途径,必须是以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反革命的暴力。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普遍规律(当然,这不排除在极个别的、敌人完全丧失抵抗力的特殊情况下,可能存在和平发展的例外)。
3.3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的政治形态
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来代替它?列宁果断而清晰地回答: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是通往彻底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过渡时期。
列宁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双重历史性质:它既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最广泛的、史无前例的真正民主;同时也是对被推翻的、企图进行反抗和复辟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最坚决、毫不留情的专政。
更具思辨性的是,列宁指出,这种新型的国家,已经是一种“开始消亡的”国家,是一种“半国家”。因为它不再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人的专政,而恰恰是多数人(无产阶级与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随着阶级的逐步消灭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它作为暴力机器的职能,也将逐步地“自行消亡”
3.4苏维埃:专政的“终于发现的”实现形式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什么?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中看到了雏形;而列宁则从俄国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自发创造的“苏维埃”(即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委员会)中,找到了“终于发现了的”政治形式。
苏维埃,这种建立在生产单位和地域基础上的、由人民直接选举并可以随时撤换其代表的权力机构,它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虚伪的“三权分立”,实现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高度统一,它是无产阶级直接行使其民主与专政权力的最有效、最彻底、最能体现群众参与的工具。
第四章:革命的同盟军——世界革命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4.1从“工人”到“工农联盟”:东方革命的伟大战略
列宁主义的第四个伟大贡献,在于其对农民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创造性解决,这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从单纯的“西方”事业,一跃转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东方”风暴。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赢得并巩固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想象的。第二国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死守着“农民是落后的、私有观念严重的阶级”这一偏见,而不敢、不愿发动农民,这最终导致了他们在革命面前的无所作为。
列宁则以其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和对俄国社会阶级力I量的精确估量,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伟大战略。他明确指出,农民中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地领导他们,以“土地归农民”的纲领完成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并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通过合作制将劳动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4.2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的“后备军”
列宁的革命视野,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以惊人的敏锐洞察到,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范畴,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同盟军。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统治与繁荣,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超额利润的吸血之上的。因此,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次反抗,都是在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后方”,都是在从根本上削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
4.3“两个洪流”的汇合:国际主义的崭新篇章
正因如此,列宁主义所蕴含的国际主义,拥有了全新的、更为广阔和深刻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两个伟大洪流”的最终汇合与合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充满磅礴力量的伟大号召,取代了马克思时代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了帝国主义时代更为响亮、更具时代特征的革命口号。
它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战略视野,使其真正成为了指导全世界(尤其是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普遍真理。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继承、捍卫、发展”的辩证统一
5.1辩证的统一:对“马列”关系的再澄清
现在,我们可以正面回答那个充满争议与迷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什么不同?”
我们必须坚持的答案是:在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最终历史目标(即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上,二者是完全一致、彻底一脉相承的。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革命的战略战术和理论的侧重点上,后者是前者的继承、捍卫与具有时代特征的发展。
列宁主义是100%的马克思主义。
它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列宁的一生,首先是一位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捍卫者,他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长期斗争,就是一场抢救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的伟大斗争。
列宁主义又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它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僵化遵守或刻板模仿,而是对其科学方法、辩证精神的大胆而创造性的运用。它勇敢地、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时代,所未能或无需详细回答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崭新历史课题。
5.2从“一般规律”到“具体实践”的伟大跨越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理解为更多地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历史总趋势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历史使命;那么,列宁的贡献,则更多地是解决了在新的、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具体地、实践地去实现这一使命的道路、战略和最有效的战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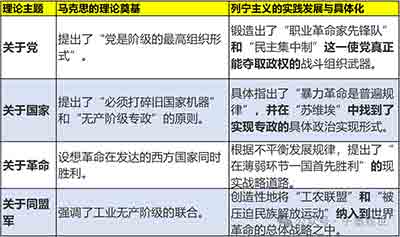
5.3历史地位:斯大林的经典总结
斯大林对此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成为经典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进一步强调:“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这一定义,科学而准确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性特征、坚韧的实践品格及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历史地位。它既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绝对继承,又凸显了其在革命实践(特别是先锋队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伟大发展。
结论: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列宁主义是唯一的旗帜
综上所述,“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其逻辑是清晰的、完整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它绝非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俄国版”或“修正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在步入其发展的第二个伟大阶段,是唯一能够指导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取得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纲领。
它的理论核心,是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刻、精辟的分析;它的革命灵魂,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不妥协的学说;它的组织利剑,是关于先锋队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的广阔同盟,是遍及全球的工农大众与被压迫民族。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性时代,其根本性质上,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帝国主义的金融霸权依然阴魂不散地笼罩全球,垄断资本的剥削日益走向极端,地区战争的阴影从未真正远去,而修正主义的思潮和政治背叛也从未停止。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时代里,任何试图“绕过”列宁、直接“回到”马克思的企图,要么是出于理论和历史上的幼稚无知,要么就是出于政治上的怯懦与向改良主义的投降。
一个抛弃了列宁主义(特别是其关于先锋队建党原则和国家专政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历史结局,必然是沦为一个无害的、温和的、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容忍的“清谈客”。
因此,面对那些试图污蔑或曲解“列宁主义”的指责和围攻,我们必须以百倍的理论自信和坚定的革命勇气,去最彻底地捍卫、去最清晰地重申、去最自觉地践行它。因为在今天,坚持列宁主义,就是最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背叛列宁主义,就是最可耻地背叛马克思主义。
这面在一百多年前由列宁高高举起的、染红了十月革命炮火、饱经风霜的旗帜,是指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一面永不磨灭的旗帜。它的理论和实践的磅礴之力,深刻铸就了后来者在广阔世界、不同国情下探索真理、开辟新路、走向人类最终解放的坚实基石与不竭指引。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