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诞辰百年 | 消费主义如何制造现代空心人
消费主义依赖的正是我们的“不幸福”——它通过不断制造新的欲望,将人推向永恒的不满足状态,甚至将自我也变为一件待售的商品。从身份焦虑到自我表演,从模仿偶像到内在分裂,我们如何在消费的洪流中重建真实的自我?
2025年,是齐格蒙特·鲍曼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重读他关于消费社会的深刻批判,愈发感受到其思想的预见性与现实穿透力。在他看来,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演变为一项永无止境的欲望制造工程。鲍曼犀利地指出,消费主义依赖的正是我们的“不幸福”——它通过不断制造新的欲望,将人推向永恒的不满足状态,甚至将自我也变为一件待售的商品。从身份焦虑到自我表演,从模仿偶像到内在分裂,我们如何在消费的洪流中重建真实的自我?本文通过鲍曼与记者哈夫纳、学者瑞恩·罗德的对谈,重新审视消费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空心人”,并探讨在这样一个被欲望驱动的时代,我们能否保持清醒,重新成为积极的生活创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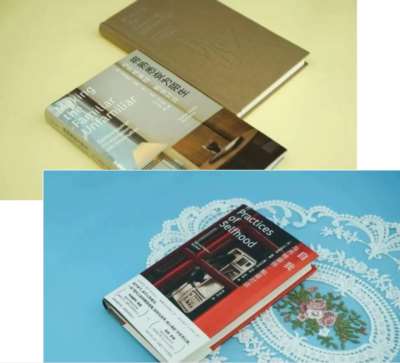
1 从满足需求到制造欲望
——消费主义如何制造“永恒的不满足”
哈夫纳:在批判当今猖獗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您讨论过身份认同如同时尚配饰的想法。您说,消费社会使人难以幸福,因为它依赖的,就是我们的不幸福。
鲍曼:在这个语境中,“不幸福”这个词太大了。但每个市场经理都会坚称,他的产品能让消费者满意。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不会有消费经济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满足,那就没理由搞产品迭代了。
哈夫纳:1968年的左翼把这称作“消费主义的恐怖”。消费和消费主义有什么区别?
鲍曼: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则是社会的特征。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
哈夫纳: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想理解这点,需要对历史进行考察。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工匠失去他们的工坊,从而陷入贫困。但新的工厂所有者——正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发展——又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工人。只要每天还有面包吃,他们就不会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现代市场经济的先驱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费经济畏惧的鬼怪就是传统的消费者,因为传统的消费者满足于她/他购买的产品。而确切地说,与先前的消费形式形成对照的是,消费主义把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而非需求的满足——关联起来。这个增长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营销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新的商品,而是创造新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片刻之前还是最新样式,还被广告描绘为欲望对象的产品,突然就会被嘲讽为“过时”的东西。下至五岁大的儿童,就被消费社会朝着不知足的消费者的方向训练了。星期天,他们会和父母一起,去一个充满有趣的、令人激动的、诱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购物。一旦厌倦,他们就会把买回来的东西扔掉。
《将熟悉变为陌生》
[英] 齐格蒙·鲍曼 [瑞士] 彼得·哈夫纳 著 王立秋 译
2 从满足需求到制造欲望
——可以通过消费而改变自我?
罗德:很久以前,彼得·斯特龙伯格曾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名人比作神灵,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他写道:名人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他们是美国消费主义最重要的中介;就像基督教的神耶稣基督一样,他们既是人又是神。他们是两个世界的参与者,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是我们向往的世界。虽然他们最初和你我一样都是凡人,但他们现在生活在我们心中的天堂,也就是广告中描绘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快乐、美丽、机智、满足、友好、富有冒险精神。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或任何当代文化的载体)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日复一日的生活。自我可以通过消费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或真实或假想的需求,它已然变成了一种基于效仿的、鲍德里亚式的宗教实践。我穿着比约恩·博格牌子的平角裤,就相当于分享了比约恩·博格的身体,正如基督徒在圣餐仪式上分享神的身体一样。同样,通过食用某一品牌的玉米片,我将自家闹哄哄的早餐桌与广告中可爱而幸福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即使我家没有过上广告中呈现的那般理想生活,我们至少与电视屏幕另一端的神仙家庭享用同样的玉米片。
乔治·卡林认为,广告应该极端写实,不应该只描绘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按照他的意思,这则广告听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嘿,老爸,等你揍完老妈一顿后,再给我来点里面掺有葡萄干的那玩意儿,行不行?”不过,广告中推销的可不是玉米片,而是宗教般虔诚的认同时刻。当广告向我推销产品的功能特性时,我可能想看到一个更接地气的广告,它应该向我呈现该产品所归属的真实场景。以推销洗衣粉或电钻的广告为例。洗衣粉广告中出现一个精通家务、会问问题的家庭主妇,或电钻广告中出现一个经验丰富、双手沾满油渍的工人,要比一个天使般年轻貌美的姑娘更让我相信产品的优越性。然而,早餐谷物食品与同类产品的竞争点是其附加的象征性价值,而不是它的口味(除非它的卖点是健康)。在时尚界——或在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探讨的艺术界,这一过程甚至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尚公司推广某种新颜色,并不是因为它即将成为流行色,而是因为这家时尚公司的推广,它才即将成为流行色。
这会如何影响一个并不喜欢该颜色的人?像往常一样,你总得做出选择:要么你引领时尚潮流,为其壮大声势,要么你自觉地抵御这一潮流。你能不去表演地做出选择吗?我认为不能。在我内心的小剧场,我仍然要对自己表演这样一出戏:我是那个拒绝顺从大众选择的人。事实上,这难道不比(可能是帕斯卡尔式地)认可最新潮流更需要一场令人信服的表演吗?
须立即补充一句:若果真如此,除了两者以外别无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伦理上完全中立的角度来思考表演。自我表演并没有错:只要我们做真实的自己,自我的表演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如果通过向自己表演我的选择,并且坚守我所珍视的价值和原则,那么将我自己划分为演员和观众就能服务于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你前面提到了米德,以及他在“客我”(me)与“主我”(I)之间所做的区分;查尔斯·皮尔士看到了“我”(me)与我内心的“你”(you)所进行的对话;社会学家们经常谈到被“我”(I)内在化,以致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的“重要他者”。如果我们同意这些观点,承认自我的内在对话性或多极对话性(polylogical),那么自我就必须不断地展演自身,不是吗?在前文,我们一致认为,即使自我在现实中是在观众面前表演,但实际发生之事,与自我在其所想象的观众面前的内在表演,是迥然有别的。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表演的效果既取决于外部观众的认可,也取决于内部观众的认可。试想一下,一位极富天赋但过于自我批判的音乐家,无论台下的观众鼓掌多久,她都认为观众只是出于礼貌,假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重大失误罢了。
《自我》
[英国] 齐格蒙特·鲍曼 [爱沙尼亚] 瑞恩·罗德 著 张德旭 译
3 身份焦虑与“自我商品化”
——我们如何把自己活成了一件待售的商品?
哈夫纳:市场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费者。就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被商品化了,这又把我们带回认同问题。
鲍曼: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哈夫纳:今天,许多年轻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发视频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还可以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没有具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对他们来说,出名意味着登上成千上万份报纸的头条,或出现在成百万上千万个屏幕上,变成人们谈论的对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们自己想要的光鲜亮丽的杂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儿。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能增加一个人在竞争中获得最多关注、名声和财富的机会。这就是编织今天的梦想和童话的材料。
哈夫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说法,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根的问题。相反,他用了锚的隐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从社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不一样,起锚既非不可逆转,也不是什么决定性事件。您不喜欢这种说法,为什么?
鲍曼:只有在我们不再是我们现在所是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变成别人,所以我们必须永远抛弃我们先前的自我。因为新的选择源源不断地出现,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当前的自我过时了,令人不满意,让人不舒服。
哈夫纳:改变我们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仍是人们的箴言:重新发明你自己!
鲍曼:当然,这一策略并不新鲜:遇到困难,掉头逃跑。人们总试图这么干。不过,新鲜的是,通过从产品目录中选择一个新的自我来逃离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线迈出的自信脚步,很快就变成强迫性的常规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变成别人”,变成了强迫性的“你必须变成别人”。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
哈夫纳:自由意味着什么?
鲍曼: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流动现代性的时代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艺术许诺了这个自由,却未能履行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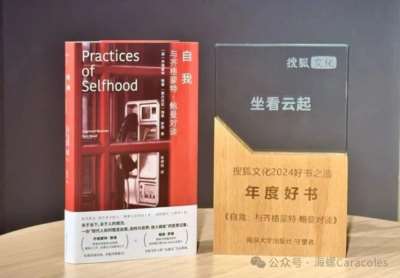
4 在消费洪流中重建自我
——做清醒的局外人,还是积极的创造者?
鲍曼: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已经成功地将人的“作业本能”转化为“消费本能”。100年前,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消费型社会;他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个新富阶层应运而生,“有闲阶层”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声望,进行“炫耀性消费”,其他社会阶层争相模仿,这极大地助长了挥霍浪费的社会风气。将人类的“期待”心理,追溯至“作业本能”,即做好一项工作的本能欲望、从尽善尽美中获得自豪感的普遍愿望、从“排出己身”中寻求幸福的心理倾向。“排出己身”这一术语,是由毛罗·马加蒂和基娅拉·贾卡尔迪最近提出的,意指为世界添砖加瓦的倾向和冲动。“消费本能”指的是对事物的占有和享受的本能,或曰“纳入己身”的本能。与“排出己身”相反,“纳入己身”是使世界日销月铄的本能倾向,是个体从世界逐一减除已转化为商品的欲望对象。
亲爱的瑞恩,你妻子这样的“硬核现实主义者”,正是消费主义经济的噩梦:他们满足于目前的消费水平,对劝诱或勒索他们继续消费的魅惑之声充耳不闻,对诋毁和嘲笑他们消费欲怠惰的谴责之声无动于衷。消费主义的蛊惑之声,一边痛斥这些消费者如此有限的需求/欲望/愿望,一边引诱那些尚未满足的消费者,让他们对新奇的、未体验过的欲望对象产生永无餍足的渴求。不足为奇,心满意足的消费者能够——也将会——为消费主义社会敲响丧钟。
如今,市场营销艺术包含双重策略,一是唤起人们对新乐趣的渴望,二是确保从中获得的快乐尽量短暂。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副作用,它使消费主义经济成为系统性过剩和浪费的经济。如你所说,人性共有的“期待”意向,一旦被消费主义经济所利用,被其商品化并重新调配,往往比人们期待的“事物本身”更令人愉悦。确实,购物行为通常比其结果,即对所购之物的占有和消费,更令人愉悦;另外,占有某物的快乐是有期限的,而购物所带来的快乐,原则上可以无限延长,至少营销大师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其延长。
罗德:你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期待”是自我构成的要件。然而,我心中所想的“期待”,其实不是期待未来从消费中获得愉悦。我期待在公园里长途漫步,但那天要是下雨呢?我期待老友来访,但我们见面吵架了怎么办?若总想着追求完美的幸福,我们终将一无所获,因为阳光与和谐的友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下雨和争吵也同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全都不可或缺。这一点常常被人遗忘,这要归咎于消费主义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每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和金钱资源都极其有限,于是,衡量成就的一个方法,就是看我们是否最为高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我们是否只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才去公园散步,我们举办的每场聚会是否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换言之,在消费主义社会,衡量成就的标准,变成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完美程度。
追求完美并没有错,只有当完美被一个定义框住,它才开始成为问题——因为运动停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完美即死亡,因为死亡也是毫无变化的。由此观之,我们或许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完美:第一种,将完美视为最终的目的地、某条轨迹的终点、人所期待的梦想成真;第二种,将完美视为无法用恒定不变的绝对标准加以衡量的东西,就像著名的视错觉中黑色方格之间的灰点一样,我们的视线永远追逐不到。显然,后一种完美可以用来保持对新鲜事物——也是更好之物——的渴望。我曾经在柏林的一面墙上看到一幅涂鸦,它巧妙地捕捉到了这种渴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什么都不会变好。”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守望者eye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