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个体的“可恨”,往往是被特定生产关系塑造的生存策略。封建礼教驯化出祥林嫂的麻木,她反复讲述阿毛的故事时,确实令人厌烦……谴责这些扭曲很容易,但真正的思考应该指向扭曲他们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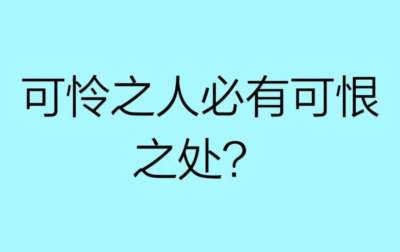
芦柴棒们蜷在破棉絮里瑟瑟发抖时,工头正捏着鼻子骂她们“自甘下贱”;阿Q被押赴刑场时,围观的看客们嗤笑着他的麻木。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成为居高临下的判词,我们是否曾追问:这“可恨”从何而来?那判定“可恨”的目光,又站在谁的立场?
个体的困境常被归咎于个人缺陷——懒惰、愚昧或短视。但翻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笔下那些酗酒、粗野的工人,他们的“可恨”恰是资本主义精密计算的结果。每日十二小时在高噪音纺织机前重复同一个动作,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微薄工资只够租用贫民窟的床铺,教育、尊严都成了奢侈品。当生存空间被挤压到只剩喘息的缝隙,所谓“道德堕落”不过是系统暴力书写的必然结局。就像压弯的树枝会扭曲生长,你不能责备它不长成笔直的栋梁。
这句俗语最隐蔽的毒性,在于将结构性罪责转嫁给受害者。它巧妙地把社会矛盾翻译成个人品质问题,让制度性的不公在道德评判中隐身。旧社会农民被迫卖儿鬻女,地主老爷们叹息着“家风不正”;996耗尽年轻人的朝气,成功学大师们训诫着“不够努力”。这种话语把金字塔式的压迫结构,伪装成公平的竞技场——你过得不好,只因你跑得不够快。于是,批判的矛头从制度设计转向了个体挣扎,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麻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可恨”,往往是被特定生产关系塑造的生存策略。封建礼教驯化出祥林嫂的麻木,她反复讲述阿毛的故事时,那令人厌烦的执拗背后,是整个宗法社会对女性灵魂的镂刻;市场竞争催生出职业乞丐的欺诈,他们的“可恨”表演,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底层生存博弈中的异化呈现。谴责这些扭曲很容易,但真正的思考应该指向扭曲他们的力量。
其实,这句判词本身就很值得玩味——谁在定义“可怜”?谁在裁定“可恨”?当贵族老爷怜悯农民“可怜”又鄙夷其“可恨”时,这种双重目光本身就在维系着不平等的秩序。真正的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赦免,而是认识到“我亦可能是他”——在另一套社会安排中,所有看似个人的“可恨”,都可能找到其滋生的土壤。

说到底,刺穿“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类话语的迷雾,不是要为缺陷辩护,而是拒绝把病症当病因。看见包身工“猪猡”般的可恨时,更须看见吃人的包身制;嘲笑阿Q精神胜利法的可悲时,不能遗忘造就这灵魂的铁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道德评判的浅滩,驶向社会改造的深水区——在那里,每一个体的困境,都与我们所有人的未来紧密相连。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