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是人类的敌人吗?
杂草不是他者,杂草就是你我。
杂草不是他者,杂草就是你我。
——迈克尔·波伦,《杂草、玫瑰与土拨鼠:花园如何教育了我》
去年以来,我跟随食通社伙伴们走访了全国十余个生态农场,从北京到长三角的沿海都市,再到广西、云南等地区。每一个农场都是包罗万象的天地,它们在规模、功能、种类方面又各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如果让我向别人介绍关于这些生态农场和生态农业的记忆和见闻,恐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直到我想到了杂草,它或许是人们可以抓住的一条内在线索,沿着它深入思考,既能将生态农场同常规农场区分开,又能绘制出不同生态农场的内部差异。
1
诞生在农业阴影下的杂草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杂草与庄稼的爱恨情仇,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持久冲突的缩影。而如何处理杂草则是最考验农民心态的问题,最能折射出生态农业和其它农业模式的实质区别。

◉在南方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一两周不注意,杂草就会疯长,甚至把作物淹没。摄影:伍娇
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哪个农场不受杂草的困扰。相比于其它生产环节,甚至相比于病虫害防治,除草又是机械与农化产品运用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想要正面地认识杂草,首先想到的往往也只是它们的食用、药用价值。不过我觉得,对于生态农业而言,杂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视角转换:借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它不仅好吃,也有助于思考。也就是说,杂草有助于我们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杂草的存在本身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初步的答案。正如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杂草则是优点尚未发现的植物,它们恰恰诞生在农业的阴影中。在万千野生物种中,成功被驯化和利用的成为了作物,不被青睐却与前者竞争的,就沦为杂草,二者如何界定取决于人类的生计和文化需求。很少人能想到,稻田中常见的“恶性杂草”——稗草(长期的筛选压力让它们伪装得与水稻颇为相似,即“瓦维洛夫拟态”),也曾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左右两株,哪个是稻子?哪个是稗子?答案在评论区揭晓。摄影:沈叶
当我们远离人类中心的视角,杂草就失去了那种不洁或危险的道德意涵,它的出现只是对被扰动的自然和土壤的一种回应,是一种“不破不立”的自然倾向。因此,在生态农业看来,杂草能修复土地之偏性,因而可能成为现代农业某些积弊的解药。例如,在土壤板结处生长的杂草往往有松土的作用,而在土壤松散处生长的杂草则擅长固土;土壤缺乏某些必需元素则有杂草能富集,某些土地的重金属污染也要由杂草来消耗。待土质恢复平衡,它们便功成身退;反之,当人们执着于除草或扰动土壤,它们便誓不罢休。
在共学交流中,实习生亮仔的一番洞见令我印象深刻:“杂草是镜子,能显露我心故”。在传统农业中,人草之争尚不激烈。除草被视为洒扫一般的日常劳作,人工锄草本身也能起到土壤保墒的作用,杂草也以多种方式为我所用,从救荒、医药、柴火、饲料到编织。现代以来,农业集约化加剧了对水土和生态平衡的扰动,杂草才成为了人类文明必须征服的自然敌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常规农业中,一味追求效率、完全忽视杂草与土地互动关系的化学除草方式,反而锻造出了“超级杂草”:就算面对草甘膦这样的强力除草剂,杂草也终究会通过突变或基因交流产生抗性。相反,生态农业的“杂草管理”,则需要农人真正走进多样性的生态,不仅是容忍或利用杂草,而且是通过合作与竞争并存、不断生成的生命互动关系来促进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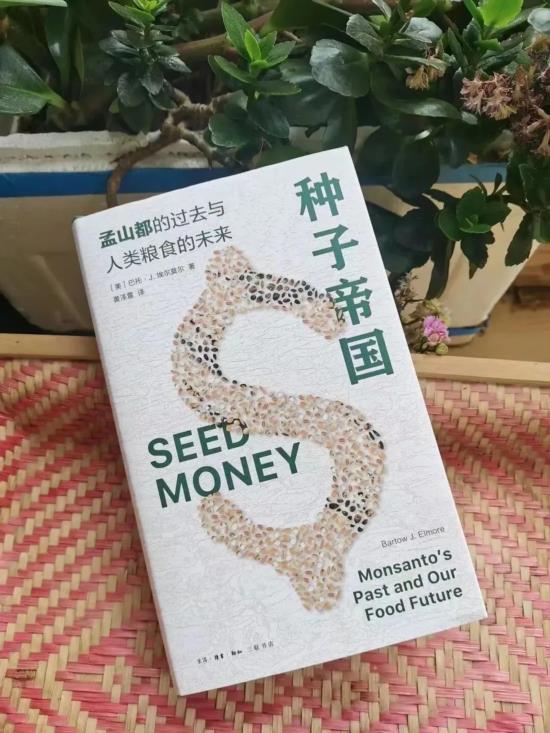
◉《种子帝国》一书揭露了孟山都的化学制品和转基因技术如何渗入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书中提到,一位孟山都资助的杂草学家因为发现除草剂抗性会带来超级杂草的问题,而受到孟山都的恐吓。图源:食通社
2
生态农业如何“与草共舞”
在生态农业内部,杂草管理方式同样是区别农人心态的关键。在不使用除草剂的前提下,杂草管理的思路大致有如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直接除掉已经发生的杂草,包括物理手段(人工除草、机械除草、覆膜等)、生物手段(生物药剂)。不过,任何单一的除草方式,都会多少向杂草施加进化压力,从而形成单一化的杂草群落。
其次是利用生态学原理减少杂草的发生,例如轮作、套种、假苗床、滴灌,乃至以草治草。这一类技术的精髓在于营造时机的不确定性和场景的多样性,让杂草难以摸清生存套路。
最后是让杂草成为构建农田生态的积极力量,当生态平衡趋于完善,作物变得更健壮,杂草也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或许与一句古谚相应:“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广西百草园农场的小伙伴正在割草,适时控制草的长势为地所用。留草可以让土壤有良好的回润功能,有助于植物根系从土壤深处吸取水分养分。摄影:陈昱均
但生态修复的理想往往不得不在农场营收的现实压力面前让步。有机种植的产量往往不及常规种植,更何况,许多生态农场启动于被化学农业污染或榨干的“病地”上,需要更长时间使之复健。有些农场选择了更直接见效的除草手段,哪怕为此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大理归零农场的玉笏姐认为,仅仅依靠这些手段的生态农场,并没有真正摆脱常规农业的思路,自然本身的修复潜能并没有得到信任和激活。
如果仅仅着眼于产量,我们也就错失了生态农业的“无尽藏”:可持续性和韧性——这意味着农作物更能应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在大理的归零农场,玫瑰树的株距比一般农场要大不少,套种着其它果树、灌木等,杂草也无所顾忌地生长。可不要小看这些杂草:拨开郁郁葱葱的茎秆和藤蔓,还有枯枝败叶和带着菌丝的腐殖质层精心呵护着表土,棕褐、松软、湿润、清新的交感扑面而来。

◉归零农场没有除草的小块农田。
玉笏姐回忆道,之前大理遭遇连续干旱时,别家的玫瑰园损失惨重,而归零农场的植株却挺过了难关。令其他农场主同样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田间横行的害虫在这里几乎找不到踪影。正是杂草群落营造的生物多样性完善了食物链,避免了特定害虫的“一家独大”。
生态农业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另一重惊喜:食物的风味。对于尝过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这无需多言。而亲临健康的土地去品尝它的馈赠,更能带给我们更鲜活和整全的滋养。玉笏姐随手从一棵李树上摘下几颗果子给我们。那酸甜多汁的欣快感让我们很难想象这棵树刚刚在农场安家时的苦涩。这棵树原是别人不要而捡过来的,头两年结的果子几乎无法下口。玉笏姐想,再等一年看看,如果还是这么苦就挖掉算了。没想到,到了下一年,也许是经过农场水土的“解毒”,果子的味道已大有改观。昔日的耐心缔造了今日的缘分。

◉归零农场的李子树。
3
“不除草”的适用范围
有人或许会质疑,“不除草”是否只适用于极小规模的生态种植场景?对于那些更需要集约化种植、与杂草竞争更激烈的作物,这是否只是一种空想?对此,生态农人不是教条主义者:除草的目的并非斩草除根,而在于减少杂草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基于不同种植条件,杂草管理的程度和方式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但总体而言,他们会尝试将除草限定在苗期等特定阶段,以及长势快、高大、根系发达的特定种类,对于影响不大的杂草则不去干涉。另外,种植规划本身也是与杂草“休战”的契机。
首先是降低对集约化的追求。如果不求将单产和一致性做到极致,少许杂草无伤大雅。归零农场有三小块地种有不同品种的水稻,对其中的稗子等常见杂草,玉笏姐说:不用拔。可以说,她已经把适量的稗草当作了农田系统中的一员,它们径自生长,并不影响水稻丰收。
其次是给杂草留出其它的场所。规模化种植粮食作物的生态农场,例如西安的绿我农场、昆山的悦丰岛,会选择休耕一季,给土地“补充”有助于恢复地力的杂草。这对于杂草和庄稼、土地和人而言都是一种喘息与和解的机会:到了下一季,茬口压力小了,施肥和除草的要求也少了。在北京的溪青农场,草莓地不留杂草,但周边会种上十字花科等吸引虫子的作物,从而发挥杂草的生态防治功能。
除了时间、空间之外,杂草和作物的界限也可以通过品种多样性而模糊化。悦丰岛承担着老品种保育的任务,在上百个水稻品种中,大约20种成行地进行扩繁,40种左右在一米见方的小田块进行保育。这些保育方还需额外用竹竿、绳子加固,并适时加装防鸟网和遮阳网。在这里,不同脾性的水稻让我大开眼界:早熟晚熟、高秆矮秆、水稻旱稻,不一而足。特别是有的高秆品种,稻叶像乱发一样弯倒,穗子也随性散开——在绝大多数其它稻田中,它们都被视为“野稻”或“杂草稻”而拔除。

◉悦丰岛的老品种水稻。据统计,在悦丰岛,共有167个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域内种植,其中包括昆农8号、白壳老来青、鸭血糯、苏御糯等62个水稻品种。
4
“外来入侵杂草”的未知命运
然而,还是有一些杂草被更严格地挡在了生态农业的边界之外。
在我遇到的杂草中,唯一让我难以抛弃成见的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它在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上海等地,凭借极强的繁殖能力和耐贫瘠的特性,逐渐向野外扩散蔓延。位于上海奉贤的乐闲谷农场,部分闲置地块在短短数年内已经成为这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天下。一人多高、茎杆木质化的植株密匝匝地疯长,其化感作用将周边草本植物悉数扼杀在摇篮里,俨然植物界的法西斯主义者。袁清华老师每年都会带人在开花之前把它们砍伐一遍,但此类措施只能暂时控制它的爆发。

◉袁清华老师正在用镰刀割加拿大一枝黄花。
那几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除草。割草机只能处理一些低矮的草,成片的加拿大一枝黄花都需要靠人工,使用镰刀或者电锯。袁老师耐心地纠正我的动作细节,待我逐渐熟练,一刀下去,一排植株倏然倒地。一种油然而生的战意罔顾汗流浃背、精疲力竭,驱使我踏着断枝不停地向荒地深处推进。这是比常规农业更决绝的敌我关系:实际的生产需求升华为道德使命感。
我的感受不是孤例。在交流中,一些希望少除草或不除草的伙伴,也难免对那些恶性杂草抱有敌意。这或许基于如下原则:以互惠、包容为原则的生命可以共存,以侵略性、排他性为原则的生命需要被遏止。因此,铲除恶性杂草是改良农业生态的“必要之恶”。
“外来入侵杂草”不只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本身也包含着人类的活动因素。首先,从早期殖民历史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迁徙与势力扩张,让某些物种搭上了顺风车。其次,外来杂草发生最严重的地区,往往也是规模化垦殖、化学农业、工业与城市建设显著扰动的土地,本土生态系统的削弱,客观上为外来者扫除了本就有限的竞争者和天敌。
即使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只能接受加拿大一枝黄花来到这片土地的事实,并且谁也无法预测它的未来命运。也许可以利用本土的杂草与之竞争,也许会有新的天敌来对付它,也许人类又开发了它的新用途。但这需要时间,也不可避免让本土的人和其它物种受伤害。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这片人类持续扰动的土地上,它很难就此消失。
或许,更早到来的三叶鬼针草能给我们多一点底气。从生态学来看,它并不是个良好的演替物种,但它也客观上修复着被扰动、被污染的土地,通过自身的多种用途而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云南丽江的石头城,它和本土的近亲一样,凭借广泛的用途(药用、饲料)而嵌入了本地人的知识体系,纳西语名字已难以让人想起其入侵性的来源。在颜萍姐的百草园,鬼针草还成为了餐桌上的野菜。原来,传统农业社区和生态农人并没有机械地划定本土与外来物种的边界,也没有把所谓“恶性杂草”上升到敌我关系。这些杂草带来了麻烦,但也有转化的余地:至少,它可以吃。

◉在位于广西的百草园农场,鬼针草作为野菜被端上餐桌。
绕了一圈,“思”又回到了“吃”。正如人类学家安娜玛丽·摩尔所揭示的,吃和喂养关系塑造了不同物种生命的基本连结。人类以相反的方式同时喂养了庄稼和杂草,也以相反的方式吃掉它们。毕竟,任何有限的生命都不自足,草也好,人也好,终究要学会与环境中的其它生命共存,相互取予。当农场的羊欣然接受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美餐,我对这种杂草也少了些偏见。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