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思维与存在的辩证法:对一些哲学概念的说明
每一个试图把握自身命运的阶级、每一个投身革命斗争的个体都无法回避的思想原点。
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从始至终都缠绕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哲学家坐在书斋里凭空杜撰的抽象命题,而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必然遭遇的现实矛盾,是每一个试图把握自身命运的阶级、每一个投身革命斗争的个体都无法回避的思想原点。马列毛的哲学著作,从来不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罗列,而是对思维和存在这个根本矛盾在实践中展开过程的科学剖析;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所有哲学概念,也绝非散落在认识史上的孤立碎片,而是思维与存在这对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认识维度上的具体表现,是这一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要理解这些概念的统一性,就必须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内在矛盾出发,通过分析其自身的辩证运动,揭示它们如何一步步从这个根本命题中衍生出来,又如何共同构成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完整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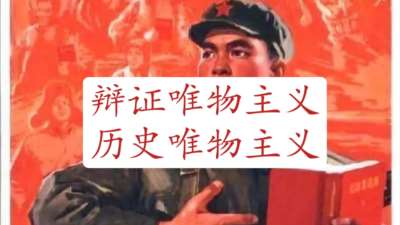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表现为“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这是人类认识活动得以展开的第一个逻辑前提。当原始人拿起石块敲击猎物、当奴隶在田间耕作思考收成、当无产阶级在工厂里审视机器与自身的关系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思想、愿望、计划(即思维)与眼前的自然界、工具、剥削者(即存在)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直接关乎生存与斗争的实践问题。如果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即人的意志、观念可以任意决定现实,那么原始人就会相信仅凭祈祷就能获得食物,奴隶就会寄望于奴隶主的仁慈来改变命运,无产阶级也会幻想通过道德说教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就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实践本质,是剥削阶级用来麻痹劳动人民、掩盖现实矛盾的精神鸦片。而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革命阶级的思想武器,恰恰因为它直面“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一不容置疑的实践事实。自然界先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社会存在(首先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从“存在第一性”这一根本前提出发,我们必然分析出“物质”这一哲学范畴。马列毛主义所说的物质,不是朴素唯物主义眼中的某一种具体实物(如金、木、水、火、土),也不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静止不变的原子,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这个定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抓住了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客观实在性,而不是停留在对具体物质形态的感性直观上。当我们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实际上就是说客观实在是人类认识的最终来源,思维无论多么抽象、多么复杂,都不能脱离这个客观基础。那么,意识又是什么?意识不是唯心主义所宣称的“绝对精神”或“主观感觉的集合”,而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从无机物的反应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从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到人类意识的产生,这是一个漫长的物质进化过程;同时,意识更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正是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中,人脑得以发育,语言得以产生,人类才获得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因此,意识的本质是“人脑的机能,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依赖于物质(人脑),内容来源于物质(客观存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运动埋下了更深层的伏笔。
物质不是静止不动的,这是我们从“存在第一性”中分析出的又一重要结论。如果物质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那么人类认识就会停滞不前,社会也不会有发展和变革,革命更无从谈起。但实践告诉我们,从宏观的宇宙天体到微观的基本粒子,从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唯心主义往往把运动归结为精神的运动(如“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则割裂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要么认为物质是静止的,要么认为运动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客观实在的基本属性。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但绝对运动中又包含着相对静止,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这种相对静止不是运动的中断,而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正是因为有相对静止,事物才能被我们认识和区分,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概念,人类社会才能在变革中保持必要的连续性。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内部矛盾不断运动变化,但在未被社会主义取代之前,它始终保持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这种相对静止是我们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前提。
物质的运动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成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具有一维性(不可逆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具有三维性。时空不是唯心主义所认为的“人的感性直观形式”,而是物质自身固有的属性,具有客观性。就是说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物质的运动都离不开时空。同时,时空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时空的客观实在性是绝对的,而时空的具体特性(如时空的伸张性、持续性)则是相对的,会随着物质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这已被相对论所证实)。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把时空理解为脱离物质运动的“绝对时空”,认为时空是永恒不变的“容器”,这就割裂了时空与物质的辩证关系。
物质的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着自身固有的规律。规律是“物质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重复性。规律的客观性意味着,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万有引力规律始终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剩余价值规律始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唯心主义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把规律归结为“神的意志”或“人的主观约定”;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则虽然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但却看不到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承认规律客观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通过实践认识规律,并运用规律改造世界。这正是革命的哲学依据,无产阶级不是被动地受历史规律支配,而是通过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主动地开展阶级斗争,利用规律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正是思维与存在矛盾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即思维通过认识规律(把握存在),又通过指导实践(改造存在),实现了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把握。
从“思维能否认识存在”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分析出认识论的全部内容。这一问题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它直接关乎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不可知论者(如休谟、康德)认为,思维无法认识存在,或者无法彻底认识存在。休谟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认为它只是人的主观习惯;康德则认为,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无法认识事物的“自在之物”(本体)。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会导致消极无为的结论,因为如果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么人类就无法改造整个世界,革命也就失去了理论前提。马列毛主义哲学坚持可知论,认为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这一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实践是连接思维与存在的桥梁,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同时,实践又能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会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反之则会失败。而这些实践最终都属于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它不仅概括了当下的实践活动,也将过去实践及其衍生的正确经验和逻辑实现统合。
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具有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体现在,实践的主体(即人)、客体(即客观世界)、手段(即工具)都是客观的,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也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实践的自觉能动性体现在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动物只能适应自然,而人则能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体现在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并且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实践(如阶级斗争、社会改革)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也是阶级社会的根本推动力;科学实验是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实践活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革命中,实践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既改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也改造了自身,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双重变革。
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认识的初级阶段是感性认识,它是对事物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形式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感觉是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如看到资本家的工厂、听到机器的轰鸣),知觉是对事物整体属性的反映(如感知到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场景),表象是对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回忆和再现(如脑海中浮现出工厂剥削的画面)。感性认识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但它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即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如“剩余价值”概念概括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判断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断定(如“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推理是由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过程(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推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理性认识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但它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客观事物。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实现这一飞跃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二是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要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工厂、农村,收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具体材料(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然后运用辩证分析法,从这些具体材料中概括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认识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而是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也是更重要的飞跃。因为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比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性认识),这一理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才能检验其正确性,才能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还体现在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上。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具有客观性,即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标准(即实践)也是客观的。同时,真理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的绝对性(即绝对真理)指的是,任何真理都包含着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内容,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真理的相对性(即相对真理)指的是,任何真理都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事物的近似正确反映,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会不断深化和发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真理绝对化,将真理推导成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而唯心主义则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马列毛主义哲学坚持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认为真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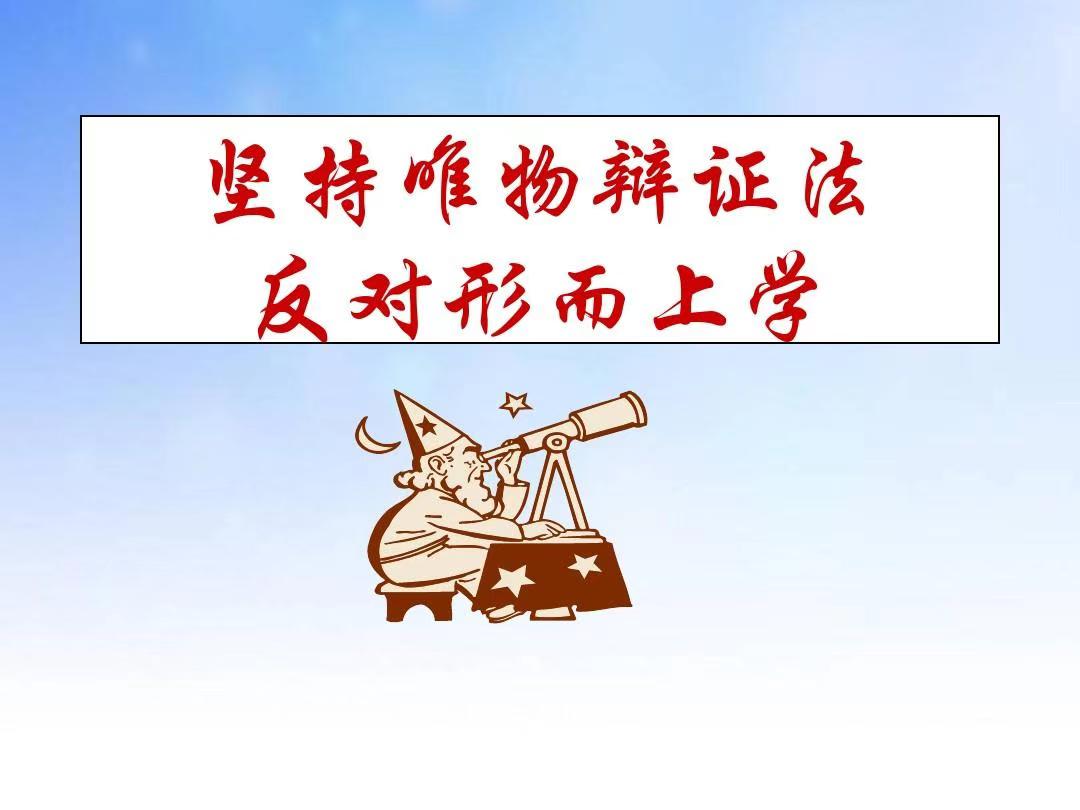
纵观人类认识史,它们都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衍生品,是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认识维度、不同实践阶段的具体展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是人类认识的起点,也是人类实践的终点。人类通过认识这一矛盾(即思维把握存在),又通过实践解决这一矛盾(即思维改造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概念、新的认识,推动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马列毛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这一矛盾的辩证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今天,我们学习这些哲学概念,不是为了背诵抽象的定义,而是为了运用它们来分析现实矛盾,指导实践斗争,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正是马列毛主义哲学的革命本质,也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最终归宿。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