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破“人性化”的面纱,重铸革命的战旗——对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彻底批判
影响力不等于正确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照妖镜下,这本书的原形毕露。它不是一部帮助读者走近真实鲁迅的指南,而是一瓶包装精美的、散发着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气味的思想麻醉剂。它的流行,恰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严重丢失的产物。
前言
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1992年初版)是在......复辟关键时期出版的一部影响广泛的鲁迅传记。本书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鲁迅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但其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本文将以彻底的革命马列主义立场,系统批判该书的三个核心谬误:一、以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取代阶级分析,将鲁迅从革命家歪曲为孤独绝望的“人性”探索者;二、阉割鲁迅思想的革命飞跃,将其后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描绘为外在的、勉强的“适应”,否定世界观改造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三、其整体叙事客观上迎合了90年代后“告别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潮,将鲁迅工具化为消解革命精神的文化符号。对这书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旨在澄清鲁迅的革命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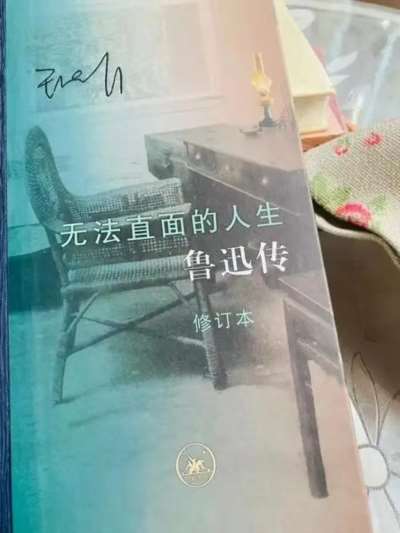
一部必须清算的“经典”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自1992年问世以来,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被许多人视为理解鲁迅内心世界的“必读书”。然而,影响力不等于正确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照妖镜下,这本书的原形毕露。它不是一部帮助读者走近真实鲁迅的指南,而是一瓶包装精美的、散发着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气味的思想麻醉剂。它的流行,恰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严重丢失的产物。在当代,阶级斗争形势空前复杂尖锐,彻底清算这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还原鲁迅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本来面目,不仅是学术争鸣,更是一场争夺历史解释权、文化领导权和青年一代思想的尖锐政治斗争。
一、核心谬误一:以抽象“人性”与“痛苦”取代阶级分析,将鲁迅唯心主义化
王晓明这本书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其观察鲁迅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抽空了鲁迅思想及其斗争实践所处的具体阶级关系和历史条件,将鲁迅一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简化并归结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抽象的“人性”挣扎和内心“痛苦”。
1. “无法直面的人生”——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
本书书名即将鲁迅的人生定性为“无法直面”。这一定位,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鲁迅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层面的、关于人生意义或个体存在的困境。这种论调,完全掩盖了鲁迅所处时代的最本质的特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危机。鲁迅所“无法直面”的,难道是他个人的生死虚无吗?不!他“无法直面”的,是旧中国“人吃人”的残酷现实,是民众的麻木与苦难,是反动统治的黑暗与腐朽。他的痛苦,首先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面对黑暗现实的阶级义愤和战斗焦虑,而非一个存在主义者对生命荒诞性的形而上学哀叹。王晓明将这种深刻的阶级痛苦,降格并扭曲为一种个人化的、带有悲观色彩的“心理不适”,这就在起点上抹杀了鲁迅斗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2. “孤独”、“绝望”叙事的资产阶级属性
本书耗费大量笔墨渲染鲁迅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固然,鲁迅作品中确有此类情绪流露,但王晓明的解读是片面的、非历史的。他笔下的“孤独”,被描绘成一种先验的、属于天才人物的宿命。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鲁迅的“孤独”,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未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时的必然局限;在后期,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种“孤独”则更多地表现为与一切反动势力及错误思潮坚决斗争时所必需的、战略性的“韧的战斗”的姿态。他的“绝望”,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反抗的绝望,是“与黑暗捣乱”的战术性表达,其本质是反抗,而非屈服。而王晓明将这种战斗的、积极的“绝望”,解读为一种消极的、近乎虚无的悲观主义,这完全歪曲了鲁迅精神的实质。这种解读,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脱离人民斗争时常有的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是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强加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身上。
3. “国民性批判”的静止化与精英化歪曲
本书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解读。王晓明将鲁迅对民众“愚昧”、“麻木”的批判,描绘成一种近乎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绝望看法。这完全背离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启蒙立场和“立人”的崇高目的。鲁迅批判国民性,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为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其出发点是对人民的爱,其归宿是人民的觉醒和解放。而王晓明的解读,则将鲁迅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对群众充满失望的精英主义者。这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篡改了革命家鲁迅与人民群众应有的血肉联系。这种解读,在客观上为否定群众、蔑视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张目,是极其反动的。
二、 核心谬误二:阉割鲁迅思想的革命飞跃,否定世界观改造的进步性
本书对鲁迅思想发展,特别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转折的描写,充满了歪曲和贬低。它千方百计地淡化、模糊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质的飞跃,企图将鲁迅定格在一个永恒的“怀疑者”、“批判者”的位置上。
1. 将接受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不适”与“勉强”
书中在论及鲁迅后期思想时,极力强调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习惯”、甚至“本相暴露”,暗示这种转变是外在的、非本真的,是为了斗争需要而进行的某种“妥协”或“伪装”。这是对鲁迅最大的侮辱!鲁迅自己曾清晰地说过,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被创造社逼出来的”,但结果是豁然开朗,“救正了我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是一个伟大的、真诚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事实面前勇敢地否定旧我、接受新知的典范。王晓明却将这一光辉的、充满喜悦的思想解放过程,描绘成充满内心撕裂的痛苦过程,这完全是对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态度和巨大收获的污蔑。其目的,就是要割裂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血肉联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和强大生命力。
2. 贬低后期杂文的战斗价值
对于鲁迅后期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就的、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王晓明在不得不承认其犀利的同时,总流露出一种惋惜,认为它们失去了前期作品的某些“文学韵味”或“深邃的孤独感”。这种论调,是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和资产阶级审美观。鲁迅后期的杂文,正是因为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所以更深刻、更准确、更有力地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更有效地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其战斗性、政治性。王晓明用所谓“文学性”的尺子去衡量,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标准,这暴露了其骨子里的资产阶级文艺观。
3. 否定“世界观改造”的必然性与伟大意义
贯穿全书的一个潜在逻辑是:保持“独立”、“怀疑”的“人性”探索才是最高价值,而接受一种“主义”则意味着个性的丧失。这完全否定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鲁迅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突破了旧式知识分子的局限,实现了向无产阶级立场的历史性转变。王晓明却将这一过程视为一种“损失”,这充分暴露了其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的顽固性。他欣赏的是作为“同路人”的、充满苦闷的鲁迅,而不是作为坚定战士的、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者鲁迅。
三、 核心谬误三:客观上的政治危害——为“告别革命”论调服务
这本书出版于1992年,这个时间点绝非偶然。此时,......复辟已不可逆转,意识形态领域需要系统性地“告别革命”。王晓明的《鲁迅传》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种“告别革命”的鲁迅形象。
1. 塑造“革命悲剧论”
本书通过将鲁迅的一生描绘成充满内心煎熬的“悲剧”,向读者暗示:革命是痛苦的、撕裂人性的,甚至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一个像鲁迅这样深刻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痛苦,普通人更应远离革命。这种叙事,与“稳定压倒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告别革命”论调高度合拍。它企图让人们相信,革命是一种值得同情但不应效仿的、代价高昂的“理想主义冲动”。
2. 将鲁迅工具化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偶像
本书着力塑造的鲁迅,是一个主要进行文化心理批判的“孤独的批判者”形象。这个形象,恰好可以被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引为同道。他们可以借此宣称:真正的鲁迅是“独立”于任何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的,是永恒的“政府批判者”。这样一来,鲁迅就被工具化了,被抽去了其最终走向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变成了一个适合资产阶级学术体制和公共话语的“批判知识分子”符号。其目的,是消解鲁迅革命的、党性的的一面,使其批判的锋芒失去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指向,转而成为一种在体制内“撒娇”式的、无害的“异议”。
3. 瓦解青年的革命斗志
这本书对青年最大的毒害在于,它用感伤主义的、非历史的“人性”叙事,磨平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棱角。它让青年在同情鲁迅“痛苦”的同时,却远离了导致这痛苦的真正根源——阶级压迫,更忘记了鲁迅指出的唯一出路——革命。它引导青年沉溺于个人的、小资式的感伤和虚无情绪,从而瓦解其投身于改造社会的集体性、政治性革命行动的意志。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精神上的“去势”。
结论:捍卫鲁迅的革命本质,进行彻底的意识形态清算
综上所述,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一部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严重原则性错误的著作。它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系统地歪曲、阉割和否定了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本质,其客观效果是为特定时期的“告别革命”思潮服务的。
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的任务在于:
1. 必须恢复鲁迅的本来面目: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怀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内心矛盾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其主流和方向是不断前进、不断革命的。
2. 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鲁迅,必须始终将其置于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宏大背景中,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绝不能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的泥沼。
3. 必须让鲁迅的精神为现实斗争服务:在今天......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需要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学习他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后愈加锋利的战斗艺术。我们要让鲁迅的战旗,在今天的思想文化战场上继续高高飘扬。
对王晓明这本书的批判,是一场争夺鲁迅、捍卫革命历史解释权的斗争。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斗争。
打倒一切歪曲鲁迅的反动谬论!
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继承鲁迅的革命传统,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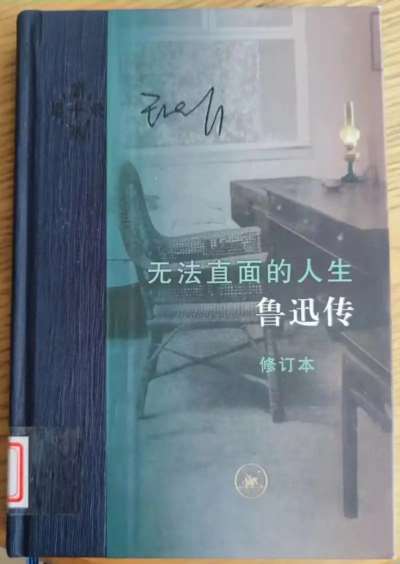
看了一些人的书评,感觉难评,是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它们生动地展示了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如何在读者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下面以战斗的马列主义立场,对这些评论进行彻底的批判。?
一、 对“高没”评论的批判:典型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与唯心史观?
这位读者的评论,代表了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影响较深、具有一定思考能力但阶级立场模糊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认识。其错误在于:?
1. 鼓吹“超阶级”的“还原历史”,掩盖阶级斗争本质。 他认同序言中“对历史的无知与简化导致无法看清现实”的观点,看似深刻,实则抽掉了历史的阶级内容。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了解阶级斗争,就谈不上真正的“还原”。他所谓的“回到时代”、“还原处境”,恰恰落入了王晓明的陷阱——即把鲁迅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将其矮化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个人心路历程。这完全掩盖了鲁迅斗争的反帝反封建的、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质。?
2. 为资产阶级“主观性”辩护,放弃马列主义的党性原则。 他承认该书“主观成分无法避免”,但认为“只要有根据不牵强附会总是有价值的”。这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论调!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学术研究都有其阶级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主观”,而在于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服务。王晓明的“主观”,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人性论来曲解鲁迅。对这种“主观”,我们必须坚决批判,绝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加以容忍。马列主义的研究,公开申明其无产阶级党性,与一切资产阶级“主观”划清界限。?
3. 大肆渲染“痛苦悲剧论”,完全歪曲鲁迅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内核。 该读者全盘接受了王晓明对鲁迅“痛苦”、“孤独”、“悲剧”的描写,并得出了“鲁迅终于死了是一种解脱”的荒谬结论。这充分证明了错误传记的毒害之深!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痛苦”,是战士看见敌人猖獗、战友倒下的悲愤;他的“孤独”,是先驱者“荷戟独彷徨”时寻找战机的坚韧。其精神内核是积极的、入世的、反抗的。将鲁迅的逝世视为“解脱”,是对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的极大侮辱,是用消极颓废的资产阶级人生观,来玷污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
4. 宣扬“非政治化”的鲁迅,阉割其战斗武器。评论最后说“需要一双不被裹挟的盯着事实看的眼睛”,这更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被裹挟”的眼睛。鲁迅最可贵的,正是他鲜明的阶级爱憎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正是用这双无产阶级的“火眼金睛”,看穿了一切反动派的鬼蜮伎俩。要求鲁迅“非政治化”,实质是要求人们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而让鲁迅的批判失去锋芒,沦为无害的神像。我们今天需要鲁迅,正是需要他那种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而不是什么“多一分清明”的庸人哲学。?
二、 对“有所思”评论的肯定与深化:必须点明政治要害?
“有所思”读者的评论——“主观臆断太多,还说鲁迅后期没有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真是歪屁股”——抓住了本书的一个核心谬误,方向是正确的,但批判不够深刻。?
我们应当进一步指出:王晓明否定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简单的“主观臆断”或“歪屁股”的学术偏见,而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进攻。其目的在于:?
①割裂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血肉联系。?
②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生命力与改造力量。?
③为“告别革命”、“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反动谬论张目。?
因此,对此问题的批判,必须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看清其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反动实质。?
三、 对“Cecilia”评论的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麻醉与对鲁迅的庸俗化?
这位读者的评论,暴露了小资产阶级读者将鲁迅“工具化”以满足个人情感需求的倾向,极其有害。?
1. 将鲁迅的斗争哲学庸俗化为心理安慰剂。 从鲁迅的“别扭”中找到自己“别扭”的合理性,这是极其荒谬的自我麻醉。鲁迅的“别扭”,是与整个旧世界决裂的痛苦与坚韧;而某些小资的“别扭”,则是在资产阶级生活中无病呻吟、无勇气彻底革命的软弱性。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对鲁迅的亵渎。?
2. 企图寻找超阶级的“支撑点”,暴露其唯心主义世界观。 在“魔幻世界”中寻找“对错支撑点”,却不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清这个“魔幻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说明该读者试图回避阶级斗争,寻求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答案。而鲁迅早已指出:“一定会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是非好恶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放弃阶级立场,必然陷入迷茫。?
3. “本书会宽慰我”是最危险的信号。 将一本歪曲革命家的书视为“宽慰”,说明该读者完全接受了书中散布的消极、悲观情绪,并与之产生共鸣。这不是真正的“理解”,而是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主义,从而消解了本可能产生的革命义愤。这是精神鸦片,其作用是麻痹而不是唤醒。
四、 对“冀中草民”评论的肯定:触及皮毛,未及骨髓
“冀中草民”读者的评论,显示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嗅觉和朴素的正义感,但其认识仍停留在感性阶段,未能上升到彻底的阶级分析高度。
1. 正确指出了该书的“泄愤”本质,但未能揭露其阶级根源。
该读者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分明是写作者自己”,是“贬鲁迅的”,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因为某个时期把鲁迅抬得太高(指文革),有些人在那时受了屈辱,反过来了,总要把不平的怨气,好好出一出。”
这确实触及了问题的表象。王晓明等一批在GPCR后崛起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确实带有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对GPCR的不满情绪。他们通过“重评”鲁迅来“出气”,是确凿的事实。但其认识是肤浅的。 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出气”绝非个人恩怨,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在复辟时期,对GPCR的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意识形态反攻倒算。贬低鲁迅,是因为鲁迅后期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成为了共产主义文化的旗帜。否定鲁迅,就是为了否定鲁迅所代表的革命传统,为“告别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扫清障碍。“冀中草民”读者将其看作简单的个人“怨气”,低估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系统性。?
2. 提出了正确的防御措施,但缺乏进攻性的理论武器。?
他建议读者先读其他书(如“素笔忆鲁迅系列”)再读王晓明,“也就不至于完全被他带偏”。这是一种朴素的防御策略。?
但这远远不够。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单纯的“兼听”很容易被更精巧的谎言所迷惑。最根本的防御和进攻武器,是掌握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只有用这一锐利武器,才能从根本上识破一切“还原”、“人性”等超阶级谎言的虚伪性,看清鲁迅的革命本质。否则,读再多书,也可能只是在资产阶级学术的迷宫里打转。?
结论: “冀中草民”读者的感受是正确的,但其批判是不彻底的。他感觉到了“风寒”,但未能诊断出这是由整个资本主义...的“气候”所导致的“重病”。?
五、 对“皮皮鲁”评论的批判:在资产阶级学术框架内的精致迷茫?
“皮皮鲁”读者的评论,代表了受资产阶级“学术规范”影响较深、试图进行“理性”分析但最终陷入更深刻混乱的知识分子类型。其观点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大。?
1. 以“不可知论”为名,否定思想研究的阶级性和党性。?
他质疑“后人难以窥测”鲁迅的“内心世界”,认为从文本出发的联想“单薄”。这听起来很“严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马列主义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其社会存在(特别是阶级地位和实践)的反映。鲁迅的著作和行动,正是其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集中体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公开的、具有阶级性的文本和实践,来科学地把握其思想的主体和本质。“皮皮鲁”的论调,是为那种脱离阶级背景、大搞穿凿附会的“心理分析”打开后门,同时也是为了否定我们可以对鲁迅思想作出科学判断的权利。?
2. 用庸俗的“生活化”鲁迅,消解其革命家的战斗本质。?
他更相信陈丹青描述的“爱开玩笑、有生活情调”的鲁迅,并认为“绝望枯槁的灵魂没有生命力”。这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审美观和人性论!?
首先,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和精神生命力,恰恰来源于其对旧世界的绝望和与之决一死战的决心。他的“冷静剖析”和“淡定从容”,是战士在激烈战斗间歇的休整和观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品味”。将鲁迅的战斗力归结为“满溢外泄的智力”,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
其次,用“生活化”的细节来冲淡鲁迅的政治性,是资产阶级将革命家“去势”的惯用手法。他们将鲁迅描绘成一个有趣味的“凡人”,从而让青年忽略其最核心、最宝贵的革命精神。这是糖衣炮弹。?
3. 在“启蒙”问题上陷入资产阶级概念迷宫,完全迷失方向。?
他质疑鲁迅是否“坚信”自己是“启蒙者”,认为鲁迅是“有话要说”而非“启蒙大众”。这暴露了其对“启蒙”概念的僵化理解。?
鲁迅的“启蒙”,绝非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那种高高在上的“教化”,而是无产阶级的“启革命之蒙”。他的“呐喊”和“彷徨”,正是为了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鲁迅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正体现了他对当时那些不彻底的、甚至背叛革命的“党派”的警惕,而绝非不关心政治。他最终靠近中国共产党,证明他认清了只有无产阶级的党才能领导彻底的革命。“皮皮鲁”用抽象的“启蒙”概念套在鲁迅身上,然后又因不合身而否定它,这完全是概念游戏,其目的是否定鲁迅斗争的明确政治指向性。?
4. 其理论归宿是“异化论”,最终落入反动的文化悲观主义。?
他最后认为“在文字中还原鲁迅”是“另一种程度的异化”。这看似深刻,实则空洞。其潜台词是:任何研究和书写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扭曲。这会导致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取消一切研究的必要性。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连鲁迅的文章也不必读了,因为那也是鲁迅对现实的“异化”反映。这完全是反理性的胡说八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因噎废食,而是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
结论: “皮皮鲁”的评论,是资产阶级学术话语体系下产生的“精致的混乱”。他试图用“严谨”、“多元”的姿态来分析问题,但由于拒绝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最终只能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并以其“理性”的外表误导更多读者。
(转载自微信读书书评,有个别修改)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