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与无限:从哲学思辨到马克思的现实批判
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在于三点:一是承认政党的有限性,将其定位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中介”;二是尊重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异,通过差异的互动实现政党的自我扬弃;三是始终将无产阶级的自主实践视为革命的根本动力,避免将政党异化为“永恒工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思考过“无限”究竟是什么?

一、理论认知
当我们试图想象“无限”时,脑海里出现的“无限长直线”,其实只是“有限线段不断延伸”的运动过程的想象;我们说的“无限大数字”,也不过是“具体数字不断叠加变大”的过程的抽象。所以,当我们用“有限”和“无限”这两个固定概念去把握它们时,已经把原本“符合某种规律的运动事物”给“静止化”了。比如把“线段持续延伸”的动态,定格成“无限长直线”这个静态结果。正因如此,“无限”才会显得像超出我们经验范围的“超验之物”,仿佛它独立于人的认知之外。
于是,我们便可以明确“有限”与“无限”的核心内涵。有限,是在特定时间维度中,事物的属性、形态或人的认知处于“不变”或“缓慢变化”的状态;而无限,是在无法穷尽的时间维度中,事物的属性、形态或人的认知处于“持续变化、不断拓展”的状态。这不是说“无限”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人的认知与事物的互动关系”的体现。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若停止增长,就会觉得它是“有限的”;若认知持续拓展,就会称它具有“无限性”。

例如,我们说“苹果是有限的”,不是因为苹果本身的大小、重量是固定的,而是我们对苹果的认知已经基本停滞,或增长速度慢到可以忽略;我们说“宇宙是无限的”,也不是宇宙真的在空间上“没有边界”,而是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一直在不断增加,看不到“穷尽”的一天。
这两个例子里藏着一个关键参量——时间。从哲学视角看,时间并非独立于人的客观标尺,而是如康德所指出的“人的内感官形式”:我们对“有限”与“无限”的所有判断,都离不开自己对时间的感知框架。对苹果的认知“停滞”,是在“当下到可预见未来”的时间维度里的停滞;对宇宙的认知“无限拓展”,也是在“一代又一代人持续探索”的时间进程中展开的。换句话说,我们对无限的认知,始终以人的时间感知为核心坐标,脱离了人的历史性体验,“有限”与“无限”的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并且,我们对事物“无限性”的感知,不是事物本身的“量”在增加,而是与事物相关的“他物”的认知在增加。比如我们觉得宇宙“无限”,不是宇宙的体积在变大,而是我们发现了更多宇宙中的“他物”。从最初能看到的恒星、行星,到后来发现的黑洞、暗物质、引力波,正是这些“他物”的认知积累,让宇宙的“无限性”显得更具体。如果我们永远只知道“地球和太阳”,就不会觉得宇宙有多么“无限”。
进一步说,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有限”开始的:我们先通过有限的经验(比如看到一个苹果、观察一次星空)建立初步认知,再在历史的运动中(比如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察、实验、思考)让认知不断发展,才会把这种“持续发展”的状态称为“无限”。所以,“无限”本身是一个“虚假的超验概念”,它的真正内涵,是“有限的合规律运动”。不是“无限”真的存在,而是“有限的事物在按规律运动、发展”,这种运动让我们产生了“无限”的错觉。
数学中的两个例子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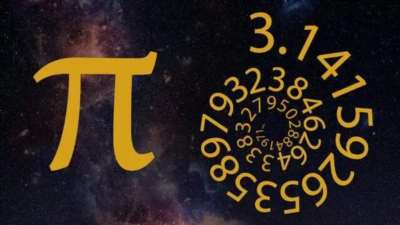
第一个是圆周率π。为什么我们说π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本质不是π本身“无限”,而是我们用来计算π的“自然数系统”是“有限的”。自然数的基础是1和0。我们的思维和电脑的运算模式,都依赖“1代表有、0代表无”的直接规定,在此基础上才细分出2、3、4等数字。这种“以1为基石”的规定,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然数系统的“有限性”:它只能描述“可分割为整数单位”的事物,却无法完美描述“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这种“不可分割为整数单位”的几何关系。当我们计算π时,其实是在“不断新建计算场景”,比如用3.14近似π,发现不够准确,就新建“3.141”的场景,再不够就新建“3.1415”的场景……每一个新场景都用新数字去补充,看似π的小数位“无限不循环”,实则是“自然数系统从有限场景,被人通过实践应用到更多场景”的过程。是我们的计算工具(自然数)的有限性,导致了π的“无限性”表象。

第二个是“0.9的循环等于1”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二者并不相等,也有人质疑是循环论证。比如“没有1,0.9的9又从哪里来?”其实问题的核心,是“思维和语言的有限性”,我们用“0.999……”这种有限的符号,去描述“无限接近1”的过程,但符号系统本身需要“一致性”,如果0.9的循环不等于1,整个实数系统就会出现矛盾(比如0.999……和1之间没有其他实数,却要被当作两个不同的数)。所以,“0.9的循环等于1”不是“被证明出来的真理”,也不是“天生如此”,而是“我们的符号系统为了保持一致,不得不做出的规定”,它本质是“有限的符号系统,在描述无限过程时的必然选择”。
从这些例子能看出,所有关于“无限”的认知,最终都要回到“人”的身上来解释。它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人的运动的、历史的、实践的认知过程”的体现。而“现实世界”本身,始终是“有限的”。它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直接影响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比如古人对“天”的认知,是“一口覆盖大地的大锅”,且有“九重天”,这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了认知;而现代人对“天”的认知,已经拓展到星系之外,这是因为物质生产方式进步让认知有了拓展的可能。
不过,很多领域的理论会陷入“抽象的无限性”误区,这正是“坏的无限性”——即一种脱离现实、只在概念中打转的无限。比如有些学者会先在头脑里搭建一套“完美的理论脚手架”,认为人类只要沿着这个脚手架一步步爬,就能实现“无限的进步”。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发展是由“现实矛盾”推动的。比如把对宇宙、π的“无限认知”,抽象成“宇宙、π本身在无限运动”,却掩盖了“人的现实矛盾才是推动认知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坏的无限性”,本质是用概念的无限,替代了现实的有限与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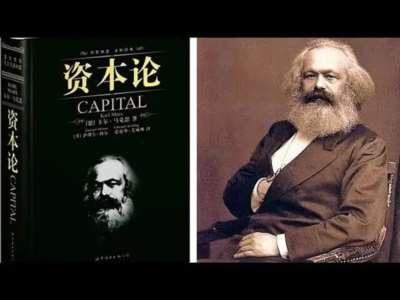
二、现实批判
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将“有限与无限”从概念拉回现实,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解放。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坏的无限性”,最典型的就是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无限扩张,会不断突破地域、民族、制度的界限,把所有社会关系都纳入“商品交换”的框架,亲情、友情、爱情,最终都可能变成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商品”。但马克思揭示,这种“无限性”是虚假的,它的根基是“工人劳动的有限性”: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是有限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工人需要休息、吃饭、繁衍后代,不可能无限产出劳动力。资本的无限增殖,必然会与工人劳动的有限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资本需要更多利润,就会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最终导致工人购买力下降,生产出的商品卖不出去,引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要理解这种矛盾的根源,还需要回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有限性”的分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作为人的实践产物,它的“有限性”体现为“特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边界”。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被异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还被美化为“自然规律”,仿佛社会的发展就是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但实际上,这种“无限性”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有限性”:生产资料被少数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这种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在“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但工人没钱买,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从“人的生存有限性”来看,马克思认为这体现为“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可能性”的矛盾张力: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受生理需求、自然规律的制约,有不可逾越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人作为“类存在物”,能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在有限的生存条件中开辟无限的自由空间。
黑格尔曾把人的自由视为“精神的自我实现”,认为只要思想上想通了,就能获得自由;但马克思则把自由锚定于“劳动实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求,更在这一过程中确证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存有限性被异化为“异化劳动”: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进行的强制性劳动;劳动产品也成了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工人的生存有限性被无限放大,而自由则被彻底剥夺。
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化”(即通过解决矛盾推动发展),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必然导致异化劳动的加剧,而异化劳动的加剧又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的反抗。这种反抗,就是“否定性的现实化”的表现,是对资本主义“坏的无限性”的否定。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否定性的现实化”不是一次性的革命行动,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展的。比如经济危机后,资本家可能会调整策略暂时缓解矛盾,但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矛盾还会以新的形式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也需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积累力量,从“自发的反抗”发展到“自觉的革命”。
三、实践路径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正是要扬弃资本主义的“坏的无限性”,将其转化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实无限性”。这种真实的无限性,不再是资本的抽象扩张,而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不断突破历史有限性的现实进程:比如工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后,不再被资本强迫劳动,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劳动,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人的发展空间却可以在实践中无限拓展,这才是真正的“无限”。
马克思强调,社会有限性的扬弃,不是通过头脑里“概念的自我运动”,而是通过“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实现。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时,就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限性边界:生产资料不再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社会关系重新回归人的本质需求。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发展不再受资本逻辑的制约,而是以他人的发展为条件,通过劳动成果的交换实现共同发展。这时,社会的有限性不再是束缚人的枷锁,而是成为推动人不断自我超越的现实基础。社会资源有限,我们就需要通过合作提高资源利用率,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正是“有限与无限辩证统一”的体现,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基于这种“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思想,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也非常清晰:无产阶级政党并非“绝对的革命主体”,而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抽象阶级意识与具体阶级存在的历史中介”。这种“中介性”决定了政党的“有限性”:它的组织形式、理论形态、斗争策略,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扬弃,不能把自己绝对化为“永恒的革命工具”。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但这一使命的实现,并非依赖政党的“绝对领导”,而是依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意识到自己需要联合起来反抗,革命才能成功。
政党作为“先锋队”,核心作用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引导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并在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提供组织保障与策略指导。但政党的作用始终是“中介性”的,它不能替代无产阶级的自主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政党只是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工具”,而非“主人”。
这种“工具性”还决定了政党的“历史暂时性”: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后,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历史使命也就随之完成,最终将走向消亡。马克思展望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国家消亡”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党消亡”的过程,因为当阶级不存在时,作为阶级代表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但历史上,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理论,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关于“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原则。将政党的有限性绝对化为无限性,认为政党可以永远存在、永远正确。将中介性的工具异化为绝对的主体,认为政党是革命的“主人”,无产阶级是“执行者”,最终陷入了“坏的无限性”。从哲学根源上看,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理论是谢林的“绝对同一性”,而非“差异同一性”,它将无产阶级政党视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将党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否认无产阶级内部存在差异和矛盾,否认党内派别的合法性。在实践中,这种理论导致了对无产阶级的压制,革命的无产者不再是革命的“主体”,而是沦为政党意志的“执行者”,失去了自主思考和自主实践的能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被异化为对政党的盲目崇拜。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变成僵化的教条。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实践本质”,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随着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异,通过差异的互动实现自我更新,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四、结语
马克思对黑格尔无限性范畴的改造,本质上是一场“哲学革命”:他将辩证法从“概念的天国”拉回“现实的人间”,将无限性从“抽象的逻辑运动”转变为“现实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限与无限不再是概念上的对立统一,而是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坏的无限性”是现实矛盾的抽象表现,“真实的无限性”则是通过实践扬弃现实矛盾的历史过程。
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在于三点:一是承认政党的有限性,将其定位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中介”;二是尊重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异,通过差异的互动实现政党的自我扬弃;三是始终将无产阶级的自主实践视为革命的根本动力,避免将政党异化为“永恒工具”。
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违背了这一核心要义。将有限的政党绝对化为无限的主体,将差异的无产阶级抽象为同质化的总体,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异化。原本为了“人的解放”的革命,变成了“为了政党存在”的革命。
马克思留给无产阶级的真正哲学遗产,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现实矛盾中追求无限”的辩证思维。无限性从不存在于抽象的概念王国,也不存在于绝对的主体之中,而是存在于无产阶级不断突破历史有限性的实践过程中。劳动创造历史,人类正是在不断改造现实世界、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创造着通向自由的无限可能。
这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现实路径。不要幻想“无限”能凭空出现,也不要被“有限”吓倒,只要立足现实、坚持实践,就能在有限的条件中,开辟出无限的自由空间。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