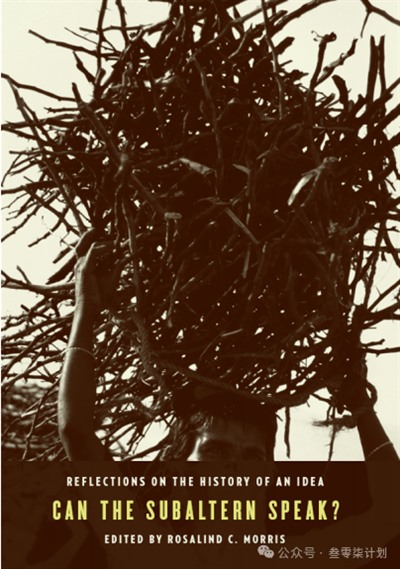比较流水线和办公室的父权程度有什么问题?
性别内部也有阶级,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空洞。我们不如在这里尝试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交叉性。
原编者按
5月29日,叁零柒更新了一篇名为《流水线和办公室,哪个更父权》的文章。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即倘若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长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标准,那么流水线女工反而走在前列。借助这个具有些挑衅意味的结论,作者希望提请大家注意通常被忽略的流水线女工的生存处境,并强调性别内部的阶级性,以最终讨论性别与阶级的交叉。
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相反,在划定和衡量女性解放与性别平等的标准上,作者复制了其想要批判的“父权”的逻辑;在制造流水线女工的形象上,作者再一次使他希望能够开口发声的人缄默;最后在提交出性别与阶级的交叉性上,Ta也再一次无意识地回到阶级的中心性。
性别内部也有阶级,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空洞。我们不如在这里尝试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交叉性。
文字| 小舟
标准设定中的诡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衡量女性解放的标准是女性从事家务劳动以及照护工作的时长,时长越短则越解放,性别关系也因而越平等。因此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算,那么被工厂流水线支配的女工相比较于有闲、有钱的办公室女性职工,自然缺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的照顾活动中,因而其在性别平等上也走在更前面。
但这样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在对比女工与白领的性别平等程度时,作者采用的指标是女性投入的时间(而不是各自家庭内女性投入时间与男性投入时间之比),这种单方面把家务和照护工作归结于女性,实际上再次让父职隐形、将女性与家庭领域的关联自然化,并最终重复性别不平等只是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判断。这是作者所重复的第一重父权的逻辑:把性别劳动分工自然化,并把性别问题边缘化。同样,这样的看法也将照护工作限定在家庭内部,将养育与血缘关系绑定,导向的结果是关爱的稀缺性(organized care scarcity)。其次,投入到家庭与照护工作中的时间与精力越少就越解放,反过来就是投入越多越落后,这实际是对养育、照护和关爱一系列之前多由女性从事的活动的贬低,这又是一重父权的逻辑。
以离开家庭领域和投入有偿劳动生活、公共政治活动的程度来衡量所谓的女性解放,这还是一种将产生于欧美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的遗产的不加辨别的挪用,这背后是将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放大为普世标准的野心,换句话来说,是殖民的企图。
印度裔历史学家Chakrabarty曾给出过一个故事:一位积极参与公共集会(部分因为其丈夫的动员)的印度女权主义活动家遭到了她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被认为是由一个核心家庭与其他的亲戚所组成的)女性成员的批评,因为她们认为:
“你真的不应该去参加这些会议。即使男人要你做这些事,你也应该无视他们。你不必直接拒绝,但你可以不做这些事,他们就会因为厌倦而放弃......你现在甚至比欧洲妇女做得还要多。”
“可是女人到底该做多少,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分寸吗?男人叫你做一百件事,女人最多做十件,毕竟男人不懂这些实际的东西!”
当然在坚持一个解放标准的人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印度女人还不够“意识觉醒”。但是如果站在她们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人们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性别关系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因此欧美女性的解放传统在这些印度女性看来可能恰恰是服从而不是反抗,因为有效的反抗是:男人叫你做一百件事,女人最多做十件,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方法做两百件。
谁在说话?
来到文章的另一个目标,即为常被忽略的流水线女工的生存处境发声,无法否认这是一种好意,或者说一种知识分子的善良。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一群人应不应该替另一群人发声,而在于发出的到底是谁的声音?
在这篇文章的描述里,流水线女工是一个典型的悲惨形象,每天都被工厂的劳动压榨,面对家人时也是同样的力不从心。说实话这不是什么需要发声才能够被人们知道的形象,在这种三言两语的勾勒中没有细节、没有情感,甚至都没有人,有的只是些陈词滥调。女工们自己认可这样的形象吗?关于她们,我们除了可怜、同情和投注政治动员的热情之外,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吗?她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怎么看待自己在照顾中的缺席?是亏欠、无奈还是已经尽力,还是都不是?在那张给出来的流水线工厂排班表里,我们看不出这些,拥有的只是对所谓生存处境的想象。
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看这本书!
作者试图为她们发声,但是实际结果是她们再一次、又一次,沉默了。想一想自己已经在很努力地活着了,但每天早上一出门听到的却是“真是个可怜女人”的感叹,我想这不是什么非常愉快的体验。这样的写作勾勒出来的流行形象过于简化,和第一部分的比较逻辑一样简化。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同样是父权的逻辑,因为清晰、单一的形象同时制造的还有作为掌控者、长官或者说上帝的写作者。“他们”掌握一切关于“她”的真理。
当然,我在这里的讨论不是要提出一种关于流水线女工的更本真的声音,并认为这种声音只有她们自己掌握,而是希望写作者的替代性发言能够再追问自己多一步:我到底在用谁的声音说话?我发出的是谁的声音?
交叉性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于交叉性的理解是:性别内部也有阶级分化,不同的人的处境是差异化的。但其通篇只强调了性别内部也有阶级,导向的结局似乎又是:不能忘记阶级的使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当然,这句话反过来说——阶级内部也有性别,同样空洞。这样的关于交叉性的理解基于把阶级、性别理解为固定的身份,而不是活动中的关系,因此我们所能想象的交叉性就只有,字面意思上的:交叉,或者插入。
我不觉得我们的讨论应该停留在这里,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我想介绍一下Bhattacharya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的讨论,以此来为进一步思考交叉性打开一个缺口。Bhattacharya区分了作为经济活动的剥削和其他形式的压迫,如性别、种族、城乡关系,在她看来,正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于性别、种族、城乡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才能够更有效的运作。举个例子,当欧美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发现性别分工的安排使得女工更容易接受低工资进行劳动,同时其生育安排使得这些女工在30岁以前就要辞职回家照顾孩子,这使得企业不需要为她们后续的衰老负责。一批随时被替换的流动廉价工人,支撑起了更为有效的经济剥削。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也讲了个类似的交叉性的问题,即工人家庭的孩子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不利于其社会流动的反学校文化,是因为他们把在学校乖乖读书视为女性化的,而只有在工厂接受磨练才能成为男子汉。在这两个故事里,性别与阶级的交叉性体现为性别关系深深地嵌入到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换言之没有这样的关于性别的安排,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很难高效运转。
出现在德国汉堡的关于交叉性的宣传标语
当然,这也只是讨论交叉性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把性别视为一种视角、一种写作方式以及一种对未来的不同想象去进行阶级的思考(或者反过来)。
毕竟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交织在一起的。
本文提及和推荐的相关书籍有: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Dipesh Chakrabarty) .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ringOppression (Tithi Bhattacharya).
《学做工》(保罗·威利斯)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