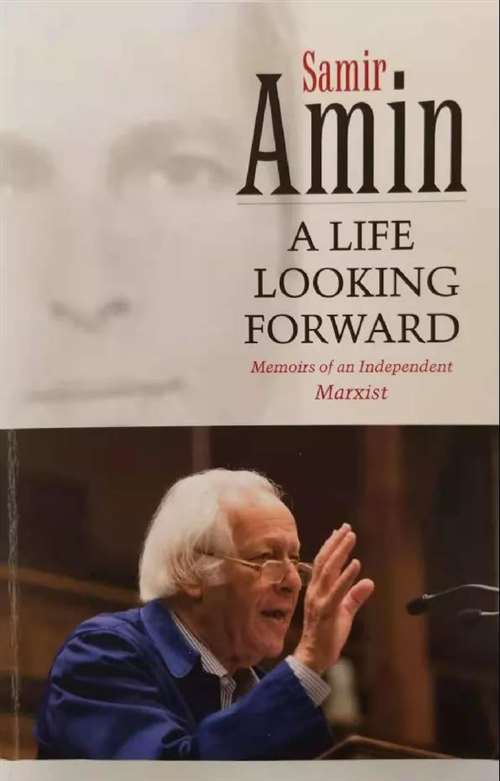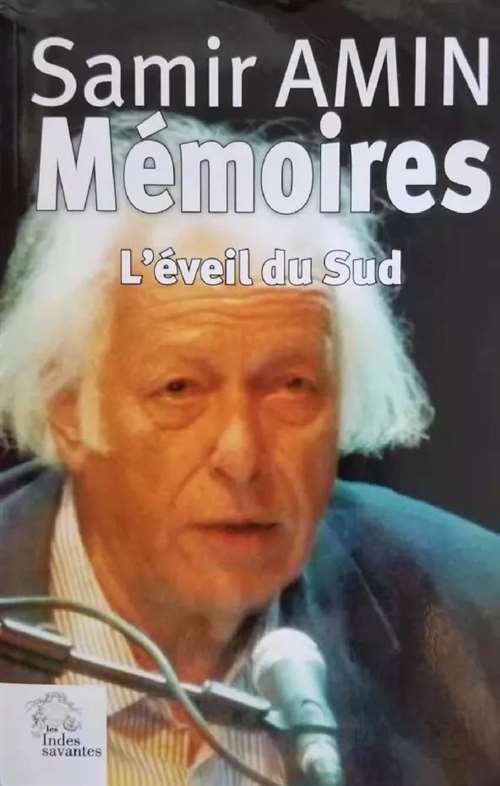无悔一生走在漫长的革命路上——缅怀萨米尔·阿明
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相交相知,是我极大的荣幸。对于这位老师、父辈、同志、朋友,我从心底里敬佩。阿明为人光明磊落、以德服人、不求名利、知识渊博、和蔼可亲、爱恨分明,但求世界变得更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走向大同。朴素真诚,见解尖锐无比。
2006年,阿明出版第一部英文版自传,题为《向前看的一生: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A Life Looking Forward: Memoir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2015年,出版法文版自传,题为《萨米尔.阿明回忆录:南方的觉醒》(Samir Amin Memoires: L’eveil du Sud)。2016年,每月评论出版社编纂他的第二部英文版自传,我参与了部分整理工作,资助了一些经费,与出版社约定,出版2年后,电子版可以上传全球大学堂网站,供读者免费下载(文末附有下载链接)。2018年8月阿明与世长辞,本书翌年问世,书名是《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萨米尔·阿明的第一部自传,2006年出版
萨米尔·阿明的法文版自传, 2015年出版
阿明以法文、阿拉伯文、英文撰写了几十本著作,中国读者熟悉的,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自由主义病毒》等。2009年,我与阿明和浩达(Francois Houtart)共同主编了《抵抗的全球化》,上、下两卷共九百多页,收进一百多篇文章,呈现了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困境和诉求。
在阿明芸芸著作里,我特别喜欢两部英文版自传。从阿明的生命故事为线串连的历史情境,读者可窥见80多年的大历史中个人的际遇、冲击、抉择与思考。既然是自传,就不用忌讳所谓的“主观”看法,加上阿明性格直率,不献媚权贵,自传里有不少让人莞尔一笑之处。例如,阿明谈到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召开时,一位欧洲富人邀请他在电台上对谈十分钟,阿明这样描述:
“达沃斯的对方问我:‘先生,为什么像您这样的经济学家没来达沃斯?’我的回答很简单:‘三个原因。一,我没有2万美元进富人天堂玩三天;二,我没被邀请,一点不奇怪,因为我的观点大家都知道;三,假如你们搞错了跑来邀请我,我也不会接受,因为我不是亿万富翁,没兴趣参加富翁的仆人俱乐部。’...‘您为什么反感亿万富翁?’‘哎,先生,这是简单的算术:90年代富翁的利润倍增,穷人的数量显然更众,可是财富增长却完全不成比例。你们要的是不平等,我们要的是平等。所以我们双方是敌对的,我看不出来我们可以怎么对话。’”(《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页369-370;下同)
有底气说这种话的阿明,不是信口开河。看看他的经历,就明白为什么他的言行有这么大的公信力。阿明把他经历的20世纪,分为三大时段:一,万隆时代的兴起与停滞(1955-1980);二,帝国主义新秩序的复苏(1980-1995);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内爆(1995)以后新全球南方斗争的推进,打造不一样的、更好的世界(another, better world)。阿明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第一时段主要是边缘/外围地区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和经济发展,第二时段主要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反扑、劫掠南方,那么,第三时段占据历史舞台的,会否是同时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发生的走出资本主义的变革?(页15-16)
从阿明的提问,当然看到,他的标尺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推进,尽管荆棘满途,磕磕碰碰。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四大师之一,阿明的去依附理论建基于他的实践、阅历、研究。1965-70年,阿明先是作为年青学生代表,后是作为埃及政府官员,参加了万隆会议。他看到帝国主义对于所劫掠的国家和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只怪帝国主义,因为本应寻求主权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以埃及为例),权力精英自身有严重缺陷,错失带领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命运,草根民众运动也力量不足,尽管埃及跟印度、中国类似,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1960年,纳萨尔政权迫害左翼,险被逮捕入狱的阿明,流亡到巴黎。2002年重回埃及,亲身接触各种政党、团体、年龄群,特别是青年一代,他总结出:21世纪开始在埃及以及整个中亚、中东、北非地区出现的政治冲突,涉及三大势力,一,声称维护民族传统,其实是民粹主义时代官僚系统的堕落腐败继承者;二,追随“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意识形态和政治;三,提出“民主”诉求但其诉求所捍卫的基本上是自由经济。这三者都承载着与帝国主义体系息息相关的买办阶级的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促使这三种势力火浴互拼,时而连系其一攻讦其余,从中渔利。(页65-66)
阿明主张,这三者都不可取,如果左翼关切的是劳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的话。左翼应该如何自处?阿明重申三大明确诉求,要坚持主权独立、经济平等、民主开放,三者并立,缺一不可。一,无论如何,民族国家内部处理纷争,不容帝国主义国家用任何借口介入;他举了美国和北约侵略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例子,强调帝国强权以民主为由延续经济掠夺。二,边缘国家要发展,不能依从三巨头(美、欧、日)的全球“分工”设计,要拒绝延续提供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依附位置。三,“民主”与社会进步、民生安逸不可分割,西方中心的民主观,不过是掩盖了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对劳动者的高度剥削的遮羞布。二次大战后的边缘国家,即便得到表面上的民族独立,甚至有表面上的经济兴起,但是上面三点无一能做到,依然在巨头构建的世界体系里。在国家内部,处于边缘的、依附的、社会动荡、经济不公、政治打压的情况,南非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国家就算有“发展”,也只能说是“流氓发展模式”(lumpen-development)。(页25-29)
我和温铁军教授等编写《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与阿明讨论,他早就笑说,全球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新兴国家”(emerging),短暂风光后,必然沦为“新陷国家”(submerging),除中国例外。2018年5月,阿明得知自己患了脑癌,他选择中国作为最后一次出国参加研讨、会见老朋友的国家。那一次,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等大师发表主题演讲,谈论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全球化的威胁,也应汪晖教授之邀到清华大学演讲,主题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也按照惯例,每次见面都跟他做视频采访。
除了从民族国家的维度来审视挑战,阿明也从人类文明面对的三大挑战提出应对之路径。一,农业问题,是亚非拉占绝对多数人口共同面对的问题,必须实现土地革命、坚持小农生产、保障食物自足。二,社会的真正民主化。三,生态危机,首先要从根本上处理,就是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走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质解决生态危机。(页16,47)
2015年10月12日,我对阿明采访时,请他说说最快乐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他说,个人来说,最快乐的,是他的童年受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宠爱与熏陶,还有他跟依莎贝Isabelle一见钟情、牵手白头皆老;最痛苦的是他的女儿的去世。在世界大事上,他17岁加入埃及共产党,仅仅一年后,传来中国革命成功的消息,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苏联解体。
他说,18岁时,中国革命惊雷传到埃及,当年他很天真、很真诚,以为资本主义丧钟已然敲响,革命之火会燎亮埃及、亚非拉各国,人类全面解放在望。采访时,他84岁,他说,历史没有那么顺畅,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爆、社会和生态濒临崩溃,迫使人类必须寻找集体的出路。他没有了年轻时的天真,但是保持着一生的乐观进取,号召大家要有勇气往前走(Audacity! More audacity!)。他依然相信,中国、越南和古巴革命,有很多宝贵遗产留给人类。
《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题目标示了阿明所笃信的革命道路就在脚下,就在前方,不论它多漫长。细读两部自传,读者会跟着阿明的足迹,遍游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与元首、平民、农民、工人等见面,领悟阿明一生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接触他的全球价值理论、去依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感受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爱与恨,如何点燃着他的革命热情与道德勇气。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