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岂能“未写即红”又“未拍即播”?——兼论钱锺书先生的“重要他者意识”
闻过则喜,喜其得闻而改之矣。——但愿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成人情世故来遵奉!
《围城》岂能“未写即红”又“未拍即播”?
——兼论钱锺书先生的“重要他者意识”
许锡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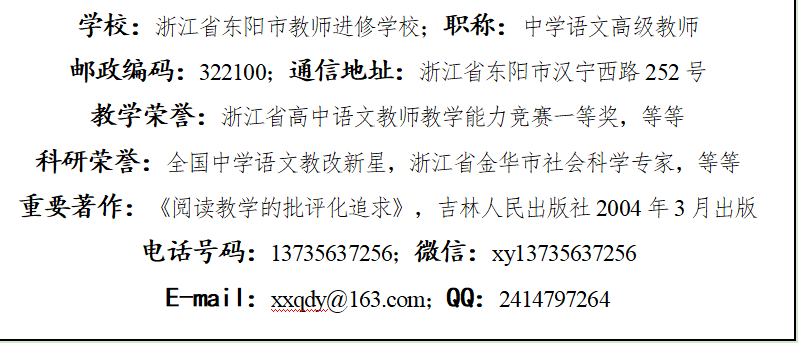
一、1943年秋季:钱锺书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岂能“未写即红”?
二、1987年:黄蜀芹所导演的电视剧《围城》岂能“未拍即播”?
三、钱锺书对黄蜀芹拍摄电视连续剧《围城》的“重要他者意识”
——————————————————————————————————
顷阅澎湃新闻,发现“澎湃号>學人scholar”专栏2020年5月15日曾经发表有《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往》,标题下明确指出,这是“文|孙守让,作者投稿”。
其实,在此之前,此文已经在《书屋》杂志2019年第9期上发表;在此之后,又在《各界》杂志2020年第10期上发表。此外,新浪和腾讯等众多网站都曾转发过这篇文章。
然而,这样一篇“一稿多投”、“一稿多发”、似乎颇受媒体宠爱的文章,其实却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史实错误,应该予以纠正,以免“谬种流传,害人不浅”。
一、1943年秋季:钱锺书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岂能“未写即红”?
孙守让同志在《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往》的开头即说:
1943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夏志清的好友宋淇在家里开派对,邀请了在上海当大学讲师的钱锺书与会,由宋淇引荐,夏志清得以见到风度翩翩、以一部《围城》名闻上海滩的青年作家钱锺书,而夏先生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青涩的文学爱好者。
1943年秋季,钱锺书还只是正式出版过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一书(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初版),又能以一部《围城》名闻上海滩么?当然不能!请看钱锺书本人在1980年2月为《围城》而写的《重印前记》中明确说: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而在1946年12月15日写作并且在1947年1月1日《文艺复兴》杂志第2卷第6期上发表的《〈围城〉序》里,他更是明确说过:1943年秋季,《围城》别说未曾出版,甚至连写作都尚未开始——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所谓“两年”,指的是从1944年到1946年,并不包括“1943年秋季”在内!
《围城》究竟何时问世?其实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曾明确交代:
1946年钱锺书刊行一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次年出版了曾在《文艺复兴》连载过的《围城》的单行本。这两部代表着战时苦心经营的作品的确不同凡响,尤其是《围城》,比中国其他古典讽刺小说都要优秀。鉴于它对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最受欢迎的小说作品。
可否平心而论,孙守让同志所谓“1943年秋天”其实应该是“1948年秋天”,此乃出于作者误写或手民误植?(“1943年秋天”中的“3”与“1948年秋天”中的“8”存在形似之处,一不小心,容易被作者误写或手民误植。)也不是的,因为早在1947年11月,夏志清已经前往美国留学,直到1983年,夏志清应钱锺书之邀回国访问,到了北京和上海,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一句话:1948年秋天,钱锺书确实已经以一部《围城》名闻上海滩,但是夏志清却已经远在美国留学,又怎能去宋淇在上海的家中,与钱锺书欢聚畅谈?
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孙守让同志虽然在写成了《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往》,但他对《围城》的《序》与《重印前记》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6章《钱锺书》却是均未仔细阅读!
二、1987年:黄蜀芹所导演的电视剧《围城》岂能“未拍即播”?
孙守让同志在《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往》结尾说到:
……正是因为得到夏志清先生的高度评价,钱锺书的声誉迅速提升,更由于1987年电视剧《围城》的上映,其名字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说到电视连续剧《围城》,我们自然就能想到其制作者中有——
导演:黄蜀芹;
编剧:孙雄飞、屠傅德、黄蜀芹;
主演:陈道明,英达,吕丽萍,李媛媛,史兰芽,葛优,吴贻弓,于慧,等等。
这里面绝大多数人,现如今都是名人,不必去读他们本人的文章,只要抓住其中一个而去“百度”一下,就可以发现:电视连续剧《围城》其实是1990年12月才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获得普遍好评,先后获得过第九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上海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十一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优秀导演(黄蜀芹)和优秀男主角(陈道明)等著名奖项……
唯其如此著名,更显孙守让同志撰写《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往》之不认真:连最基本的史实都不曾认真考辨!
将1947年提早到1943年,将1990年提早到1987年,不过差了那么三四年而已,物理时间确实相差不大,但是历史分期却是迥然有异:1943年属于战时,1947年则属于战后,“战”指抗日战争;1987年属于新时期,1990年则属于后新时期,岂可轻忽?更何况除了历史分期,此中还有人情世故等等!
“他自负精通人情世故”——钱锺书在《围城》中这样评价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方遯翁是否真的精通人情世故,根据“自负”评语的运用及其相关情节的展开即可作出判断。而《围城》能从长篇小说变成十集电视连续剧,那倒确实是有懒于相关当事人都“精通人情世故”的!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6章《钱锺书》开篇即说:“《围城》问世前,钱锺书的博学与才气,早已为其学生与朋友所称道。”一个学者怎么会写起长篇小说来呢?因为他受到了其夫人杨绛女士戏剧创作成就的激励,又转而得到了他妻子的大力支持!请看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的记载: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由黄佐临先生执导,杨绛先生在“孤岛”时期以喜剧创作成名。每当朋友聚会,盛赞其剧本上演非常成功,就有人因此而称钱锺书为“杨绛先生的丈夫”,钱锺书难免也有脸上挂不住的时候,曾作色答道:“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知道我钱锺书正在写作的《围城》的好处。”到了晚年还说过这样的话:“黄佐临导演,选中季康大作演出,票税不菲,我荣任‘杨绛之夫’。深情相助,未及酬答。”直到《围城》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并出版,深受读者喜爱,钱锺书才摆脱了杨绛丈夫的影子,赢得了自己的文学盛名。
《围城》1980年再次重印,在国内激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却直到1990年,而不是在更早的1987年,才被拍摄成为电视连续剧公开播映呢?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是小说本身的特色——“拙作实不宜上荧屏”,钱锺书一直以此为借口阻止其他人将小说制作成电视剧的努力。其他人都办不成的事情,黄蜀芹等人为什么却能办成呢?又为什么不能早在1987年就成功地走到到这一步呢?请看黄蜀芹的工作履历——
1981年,拍摄电影处女作《现代人》;
1984年,独立导演的电影《青春万岁》获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
1985年,执导的影片《童年的朋友》获首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
1987年,编剧并导演了“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影片于1988年获第五届巴西利亚国际影视录像节电影金鸟奖,1989年获法国第十一届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奖。
1989年9月5日,黄蜀芹能和编剧孙雄飞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拜会钱锺书,与她是黄佐临先生的女儿密切相关——这是身份,更与她已经历练成为著名导演密切相关——这是身价,如此身份使她有胆子去叩开杨绛的家门,如此身价则使她最终获得了杨绛及其丈夫钱锺书的器重——这中间更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杨绛,而不是钱锺书!“围在城里的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最后,杨绛当时为《围城》写下的这段话,被设计到片头里面,由毕克在每集开始前念一遍,——电视剧主题如此归纳,在多大程度上与小说本身相契合?
三、钱锺书对黄蜀芹拍摄电视连续剧《围城》的“重要他者意识”
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改编,电视剧保留与呈现了原著的精髓。黄蜀芹原本生怕钱锺书不满意,结果看完电视剧后,钱锺书却是写信向她不吝夸奖:“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在钱锺书驾鹤西去之后不久,马斗全同志曾经在2000年1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说“以我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理由是钱锺书在私人通信中称赞李汝伦“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云。此文一出,贻笑大方。因为打开私人通信,晚年钱锺书对年轻人“奖饰溢量”,称赏之甚别说在李汝伦之上者比比皆是,甚至在钱锺书本人之上者也为数不少。这当然不是因为钱锺书待人圆滑,“誉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而是因为他位高名重,有着清醒的“重要他者(the significant others)意识”,乐于奖掖后进。
众所周知,人总是按自我意识来行事的。巴赫金认为,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接壤处,“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这里,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其周围的“重要他者”对他的反应:“重要他者”认为他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他就认为自己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反之,就形成消极的自我意识。70年代美国的米勒研究了“赞赏效应”,要求对一部分二年级学生赞赏其数学才能,对别一部分赞赏其在数学上的努力。结果表示,不论以何种方式得到称赞的学生,都较未获得称赞者有较好的自我意识和数学成绩。中国古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中所隐含的奥妙又何尝不是如此?
夏志清先生曾经读过钱锺书的很多书信,他发现了两个钱鍾书:论著里的钱锺书,睥睨傲世,飞扬跋扈,逢人使棒;书信里的钱锺书呢,却是“待人过分客气了”,“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
回到“精通人情世故”上来。关于改编《围城》,黄蜀芹当着钱锺书的面非常漂亮地表态:“我们要全国人民知道,有这么一部有趣的小说,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起到普及的作用。”钱锺书对她的的答复,同样极其漂亮:“天下事是矛盾的,不普及就变成名贵。什么是‘时髦’?就是不普及。一变普及就不‘时髦’,这和人生、‘围城’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么,钱鍾书对《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的真实意见究竟如何呢?应该撇开其社交语言,而看学术评价:“诗情变成画意,一定非要把诗改了不可;好比画要写成诗,一定要把画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编是艺术的一条原则……媒介物决定内容,把杜甫变成画,用颜色,线条,杜诗是素材,画是成品,这是素材与成品、内容与成品的关系。这里一层一层的关系,想通这个道理就好了,你的手就放得开了。艺术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成品,每一本书都是成品,所以你放心好了。”
钱锺书用“诗”与“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围城》的“原著”与“电视剧”之间存在的根本的隔阂,认为“媒介物决定内容”,是艺术创作的一条根本“原则”。虽然导演和编剧尽可能的尊重原著,但是电视剧并没有能够完全展现小说的思想的复杂与深度,也不能全面的表现钱氏独特的幽默讽刺风格,甚至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无怪乎他从一开始就声明“拙作实不宜上荧屏”。所谓“每一本书都是成品”,其实是委婉声明小说《围城》和这部名叫《围城》的电视剧分属两种作品。 (参阅毕婧文章:《“拙作实不宜上荧屏”——钱锺书对〈围城〉改编电视剧的意见》,《书屋》2016年第3期)
引申出去,对我们这些“非重要者”而言,就存在着一个怎样去听“重要他者美言”的问题。对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鲁迅在序言中的公开评价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私下通信则明言:这“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着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战国策·齐策》中有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是齐威王的相国,虽然徐公是名闻齐国的美男子,但邹忌的妻、妾和客人都称赞他比徐公还美。不日,徐公来邹忌家,邹忌“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他为此“暮寝而思之”,终于洞察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的“庐山真面目”,进而进谏齐威王悬赏纳谏,广开言路,齐国大治,收“战胜于朝廷”之显效。对邹忌而言,妻、妾和客人就是他的“重要他者”。但邹忌并不听了他们的美言就沾沾自喜,而他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则在其成就动机目标设定。
在动机研究中,目标指的是成就行为的目的。成就目标理论根据个体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增长能力还是证明能力而将目标区分为工作目标和表现目标两类。工作目标是指人为了理解、掌握和创造而工作;表现目标则是指工作是为了战胜他人、证明自己的高能力或避免表现自己的低能力而工作。对于具有工作目标的人来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终结,工作的价值在于创造。同过去的成绩相比,如果取得了进步,人就会产生自豪感。对于具有表现目标的人来说则不然,其目的不是发展能力而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判断能力的标准是根据相对于他人的表现或外部反馈(如荣誉和职称等)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因而他们的目标是看起来有能力,他们可能采取走捷径的方式来实现短期目标,尽管这些捷径并不能真正促进工作。
因此,我们的动机设定,应该多一些工作目标而少一些表现目标。如此,就不会孜孜焉唯美言是听,得重要他者美言而肆意张扬,闻过则辩形于辞,怒形于色,憎形于目,甚至想方设法,打击报复,直至置人死地。相反,听重要他者对自己仅仅说一些交际辞令甚至不着边际的好评,就会明白这不见得就是对我钦佩得五体投地,而可能是别有他虑;如果重要他者偶尔有所苛求,也会不仅不怒,反而认为这是出于真心的爱护,“在科学的领域内,批评是颂扬的最高形式”(G·H·鲍尔、E·R·希尔加德:《学习论——学习活动的规律探索》第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闻过则喜,喜其得闻而改之矣。——但愿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成人情世故来遵奉!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