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尔都塞诞辰102周年】阿尔都塞|一次哲学交谈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看作是《论再生产》在哲学上的续篇,它在由《论再生产》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将哲学视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梳理了整个西方哲学史,重新阐释了西方哲学中的那些最核心的问题,如认识论、本体论、真理、主客体关系等等。
保马编者按:
今天是阿尔都塞诞辰102周年,保马特别推出阿尔都塞写于1976年的书稿《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的导言,这部书稿直到2015年才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法文版编者将其导言标题改为“格鲁乔的驴”。本文也曾于1993年在《二重字》(Digraphe)杂志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虚构了一个场景,让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齐聚一堂,就哲学问题“进行一场即兴的大交流”,最后他本人又以秘书的身份,将这场交流或争辩整理出来,形成一个可读的文本,即《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文。后者可以看作是《论再生产》在哲学上的续篇,它在由《论再生产》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将哲学视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梳理了整个西方哲学史,重新阐释了西方哲学中的那些最核心的问题,如认识论、本体论、真理、主客体关系等等。它还对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要创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是要进行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
1977-1978年,阿尔都塞以这部手稿为基础,以更通俗的方式彻底重写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形成了另一部书稿《写给非哲学家哲学入门》(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2014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这两部遗著可以看作是阿尔都塞对自己哲学观的最完整最系统的展示,它们的中译本(吴子枫译)已收入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陈越主编),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谨以此文纪念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感谢译者吴子枫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一次哲学交谈
文 / 阿尔都塞
吴子枫 译
事情是独自发生的。但还是必须让你们知道这个秘密。我有一幢房子,宽敞凉爽,夜幕降临后,还可以去大花园走走。微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音,喷泉里的水咝咝作响。那是夏天,哲学界的朋友们,也就是说,所有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被一些人的气味所吸引,带着交谈的渴望,踏着月光而来。树叶散发出清新的气息,桌上残留着吃剩的水果,还有一些咬碎的蛋糕落在沙地上。他们一个个先后到来,有的形单影只,有的结伴而行,有的是还活着的人,有的是早已死去的人,但没有人知道谁已经死了、谁还活着。苏格拉底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已经饮下自己的鸩酒;我们不知道在真理之水下颤抖的小美诺,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两个直角;不知道笛卡尔是否已经找到了他的松果体,康德是否已经完成了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是否已经或者还没有(这都一样!)颠倒黑格尔,柏格森是否已经发现了锥体的窍门,维特根斯坦是否已经得出结论:当再也没有什么可说时,就必须保持沉默……[1]。在那里,他们没有年龄,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是否在他们身后,他们的过去是否在他们面前,是否他们像在脖子后面背着一袋无花果一样扛着自己的过去,或者像在胸前挂着一个托盘以托住乳房和意识一样挂着自己的未来。作为十足的哲学家,他们住在概念的永恒性中,哲学,是“永恒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在那里居住的人,丧失了对过去和未来的所有感觉,也就是说,正如圣奥古斯丁非常完美地解释过的那样,丧失了对现在的所有感觉。由此产生了不分年龄的兄弟情谊[2],这种兄弟情谊使他们成为彼此的同时代人。在观念的无序中,是时间的大无序!他们还经常突然代替另一个人说话,或者代替另一个人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思想亲密无间。甚至彼此的惊讶,他们也能通过指尖的微动感受到。一切都已经做过和说过了,一切都如此,所以一切总是要重做和重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古老的思想更年轻,也没有什么比一种年轻的思想更古老。永恒性。当然,那里缺少女人。亚里士多德总是随身带着“自然”[3],据他解释,自然很少把女人造就得能搞哲学[4]。无论如何,尽管康德牢骚满腹,但没等妇女解放运动[5]开始,就有女人被邀请。事情在继续。天空中,群星保持着沉默。
渐渐地,随着交谈的深入,有人会想:为什么不干脆在我们之间,在生者和死者关于哲学的观念之间,进行一场即兴的大交流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尽管有所有那些已知的立场和对立[6],但至少我们可以围绕一些事情展开讨论,谁能够说,通过搅动整个那套关于真理的修辞,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不可动摇的新东西呢?这个想法本身也是自动产生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所以每个人都说,好,甚至康德也这么说。康德对别人说,哲学是一个战场,而他自己则握有永久和平的方案——两面赌胜[7]。
于是,人们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了。第一天晚上,飞快地,一个外邦人突如其来一下子引起了所有人注意,他大声说:“我要求发言!”大家面面相觑,显然,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强烈坚持着,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目瞪口呆,只有康德对身边的人说:“可我们不是在雅各宾俱乐部啊!”当那人越来越激烈地坚持时,我们看见苏格拉底抖动他的大胡子,沉着地回答说:“可是,我的朋友,要发言,你不需要先要求,因为你刚才已经发言了(沉默)。不如来反思一下这个‘发言’有多奇怪,它与世上一切被追逐的对象和一切权力有多么不同。要发言,提出要求就可以了吗?我们谁又拥有发言权,从而可以把它给你呢?[8]”关于“发言”,苏格拉底就从这里出发,像通常一样,以一系列小问题开始:我们拥有它吗?我们能把它给别人吗?我们能获得它吗?我们能保持它吗?我们会丧失它吗?发言和声音是相同的吗?声音和语言是相同的吗?等等。外邦人就这样落入了陷阱,他开始回答问题,而他自己原先的问题就隐没在了他的一系列回答中。当然,一切都会再来,真理与谬误,真理与谎言,承诺与背叛——自然,康德在这里找到了机会就“撒谎的权利”插上几句话。苏格拉底是这样一种人,他向你兜售一些毫无价值的反思,比如:要想让别人闭嘴和思考,或说话和获得真理,只要张开嘴就行。人们称之为对话。这是一种说话方式,而不是代替他人说话,好像他们有发言权一样。结果是:外邦人沉默了。但人们,不需要有会议主持,就有了反思的热情。
他们之前还有过关于“一”的讨论大会[9],在那里,巴门尼德居首位(但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因为他已经很老了,说话有点颠三倒四,所以大家任由他胡说八道)。不过人们明显感觉到,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没动,更不用说狡猾的休谟了。但空气中有太多尊敬的味道——这是个牵连着柏拉图的杀害长辈的古老故事(要成为哲学家,必须在哲学上弑父:但人们永远不会成功,我的妈啊!)——,以至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了纪念仪式。即使在哲学中,有时也必须懂得保持沉默。
相反,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却就奴隶问题吵得火热:奴隶有理性吗?还是“生来”[10]就被剥夺了理性,而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承认这值得讨论,而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在《美诺篇》上,亚里士多德难住了柏拉图:但是,对于你年轻漂亮的奴隶,你仍然赋予了他不少理性,不是吗?这个奴隶说起话来像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趁胜追击,很自然地以未来的时代作结,在未来时代,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梭会自动转[11]”。他用目光搜寻马克思,对他自己的影响很有信心,但马克思不在那里,马克思又在参加一个集会:那个神圣的国际,而且离得很远,在伦敦!
还有一场奇特的会议会让你们伤脑筋:那位认为自己一生所谈论的无非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荣耀和恩典(也就是关于上帝的一切)的尊敬的马勒伯朗士神父,却听到梅西耶·德·拉里维埃和他的重农学派朋友们说自己绝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导师;因为他曾敢于说,世界受到诸法则的支配,而这些法则是最普遍和最简单的,总之,是最“经济的”、最“有利可图的”;因为他推进了经济学思考,最后证明上帝像任何所有者一样,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农民,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最好的管家:圣米歇尔。面对这种尊崇,尊敬的神父不知如何是好,正如饶勒斯所说,它表明“少许的宗教使人远离世俗世界,但大量的宗教却能使人更接近世俗世界”。尊敬的神父不知所措。一个想投正面的人,投到了反面!他走出来,惊惶不安地怀疑自己的哲学的性质,特别是当马克思和韦伯出现之后;他寻思着,像这样沾染一切,哲学将成何体统,成为宗教本身,但“为了上帝的最大荣耀”而制造它的人并不知情。这场会议让一阵奇怪的风吹过人们的大脑:似乎人们发现,在哲学和宗教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反的关系,而且在这些联系背后,有一些对哲学来说不可或缺的现实,但这些现实却是非哲学的:比如政治经济学。似乎人们同时发现,尽管哲学中可能存在一些事件,但哲学却仍是“永恒的”。沉默。天空中,群星保持着沉默。

阿尔都塞和德里达
我相信,一天晚上,当人们最终听到下面这些有力的发言时,天色已经有点晚了。当时沃尔夫正在指责康德说:“你竭力恭维我,恭维我和其他所有人,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用你的自命不凡压倒我们。”康德说:“我是地球上最和平的人,在所有人当中,我为人说了最大的好话。不是吗?”沃尔夫说:“你难道没有说过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家,我们都是哲学家,因此,就像人眼中的狼一样,处于相互攻击的永久战争中吗?你把我们当作一个院子里相互撕咬的狗,最后,你把哲学同这些偶然的争吵混在一起,白纸黑字地写下:这只是一个战场。”[12]
列宁说:“完全正确,所有哲学家都处于战争中。但在这种哲学斗争的背后,存在着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不阶级斗争且不说”,沃尔夫(用手指着康德)说,“但这位先生把我们都当疯狗,完全是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掌握着,并且只有他掌握着永久和平的秘方,不仅是政治上的永久和平,而且是哲学上的永久和平!等他发表了自己的小册子[13],你们就会明白的。这位先生给自己分了一大份儿:战争,是别人的;和平,则是他的。等他说完话,队伍里都要保持安静!好像他不是正在通过斯宾诺莎主义的伪装发动最恶劣的战争——无神论的战争似的。何况没过多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就向我们表明了它相当于什么,他的哲学和平!”
他正说得投入,大伙开始喧哗起来。由于列宁先前支持了康德,所以最后接受打击的恰恰是他:“你说过,哲学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就更严重了,因为在沃尔夫和康德之间,最终不过是个道德问题,但随着列宁的出现,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当各社会阶级出现在记忆或遗忘的地平线上时,人们释放出了激情。但与他们所认为的相反,列宁这边并非独自一人。人们看到了伟大的马基雅维利,他因为说出了真相而在历史上受尽辱骂,他保护着这个小个子,向任何证明权力取决于其他东西而非阶级斗争的人提出了挑战。人们看到了霍布斯,他解释说,每个人都讨厌他,因为他曾经尝试在《利维坦》中提出资产阶级专政理论。人们听到斯宾诺莎解释鱼类是如何互相吞食的——从最大的鱼开始——,解释人这种带着悲伤激情的鱼,如何像其他鱼一样也是鱼。斯宾诺莎,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后,明白了其中一些道理,只简单地说:“但你们难道从来没有注意到,总是同样的人在仇恨同样的人,甚至于哲学,也总是由同样的人先开始;在这种仇恨中说话的恰恰是政治,强者和富人的政治?”人们也听到了卢梭——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的声音。他提到了社会的起源,以及富人为了让穷人臣服于自己而叫他们签署的欺诈性契约,他提到“谁构成了哲学家呢,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祭司们。”黑格尔本人也打破沉默,为的是提醒人们注意——他当然给出了《法哲学原理》中的重点引文——,你们知道吗?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积累,另一方面则是无尽的苦难。
这一局可能没有获胜,但他们不得不恢复自己的沉默。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们听到列宁说话了。
列宁说,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免费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俄罗斯农民的故事。你们得想象它发生在西伯利亚黑草原上,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一些小木屋里住着一群贫苦的人。那是漫漫冬夜,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安东(Anton),一个老人,突然被小木屋门外的反复拍打声惊醒。黎明刚刚从夜雾中升起,安东费尽全身的力气,才从床上挣扎起来,打开门,发现外面是格鲁乔(Groucha),一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很生气:“快来看!快来看啊!”他也不说为什么。最后安东跟他沿着积雪覆盖的小路来到他的田边,那里挺立着那片地区最漂亮的一棵树,一棵巨大的、用来吊死小偷的橡树。“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格鲁乔悲叹着说。安东看了看。他看到了橡树,还有一条长长的皮带,最后是一头温和的驴,它浑身结满了霜,在寒冷中等待着它所能等待的东西。“混蛋!他们把我的橡树绑到一头驴身上了!可我没法解开我的橡树!”安东一言不发,走近橡树,把驴解开。“傻瓜,这又不复杂。要解开的是驴,不是你的橡树。”[14]
他们徒劳地思索列宁究竟想说什么。
“这个故事我喜欢”,外邦人说。接着他想了一会儿,说:“在我看来,有时候要解决一个难题,就要懂得改变难题的提法,不是吗?这难道不是列宁以及所有赞成他的人所做的吗?我呢,是个外邦人,所以我完全可以跟你们说:在你们西方哲学中,有一些奇怪的成规,我并不认可,但你们却视之为理所当然。而他们呢,他们改变了难题的提法……”
“傻瓜!”苏格拉底说。
总而言之,事情大概就是这么进行的。人们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们总是要去某个地方,或者无处可去。这使得狄慈根可以说,哲学是“不通往任何地方去的道路中的道路”[15]。它从不失败。这时大家都看着海德格尔,他自称是农民,但并不开心。“你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我”,然后他以非常难以理解的解释开始,他无休止地重复着,直到人们觉得他对作为“西方”理性命运的哲学有些重要的话要说。事情大概就是这么进行的。有些人感到无聊,在讨论结束前就溜走了。在这些暂停的瞬间,人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人们只是在“点燃”问题。这是最该留在自己岗位上的时刻。然而,真是老天爷的不幸,在这些时刻,大多数宗教人士都设法溜去做祷告;政治家们都设法溜去参加集会;康德找到了拐弯抹角的逃避办法,去满足理性的一些未知的需要;黑格尔的下巴开始抽搐,显然表明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要说——但他随时准备离开,因为“弗劳·黑格尔在家里等着他”。
他们都不在了,怎么办?事情就要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首先我们约定,对所有这些会议来一次汇报,然后雇一个优秀的秘书做笔记。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马斯佩罗,由他设法出版。实在没办法。对于所有那些开溜的人(我只举了一些体面的例子,因为别忘了,哲学家也是人),要有别的方法,肯定会更少分析,不过你们还想怎样呢。我们可能会失去头绪,但我们将得到一个文本。
因此,很可惜,我们最终要删掉那些辩论的全部现场感,删掉所有那些个人的插话、口语化的措辞、故意的挑衅和出乎意料的发言,删除花园里的所有人物(花园可以自由进出,所以他们人数众多,有的是我们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并委托一位秘书来完成这项任务,对上述事情作一番概述,再把那些散乱的线索合并到一起,恢复默认的统一——它并不会太背离自己原初的杂乱无章的交流计划。
你们会看到:在某一论说的不合时宜的转折处,可能还会残留一点没有删除干净的东西,这些地方经常会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神话来看待。对待这种情况的最严肃的方式,就是承认其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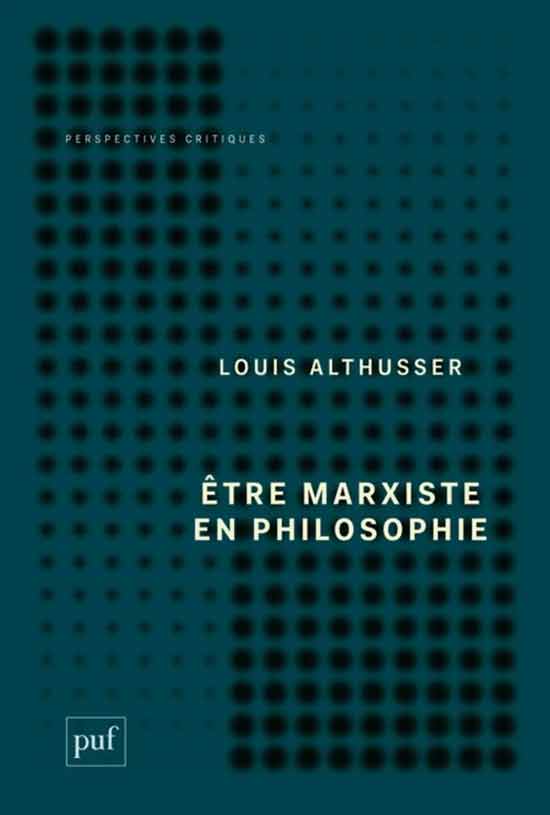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法文版,路易·阿尔都塞 著,PUF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
[1] 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5页:“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然保持沉默”。——译注
[2] “兄弟情谊”原文为“fraternité”,即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译注
[3] “自然”原文为“nature”,也译为“天性”,后文中“par nature”,一般也译为“天生”,所以“自然很少把女人造得能搞哲学”也可译为“女人天生很少能搞哲学”。——译注
[4] “搞哲学”原文为“philosopher”,个别地方也译为“探讨哲学”“进行哲学探讨”。——译注
[5] “妇女解放运动”原文为“MLF”,系“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la Femme”的缩写。——译注
[6] “对立”原文为“oppositions”,也译为“反对意见”,并可以看成是“op”(对立)+“positions”(立场)。——译注
[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在这里,人们不得不无数次地走回头路,因为他发现,他达不到他所要去的地方,至于形而上学的追随者们在主张上的一致性,那么形而上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一致,反而成了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似乎本来就是完全为着其各种力量在战斗游戏中得到操练而设的,在其中还从来没有过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得哪怕一寸土地、并基于他的胜利建立起某种稳固的占领。所以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做法迄今还只是在来回摸索,而最糟糕的是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摸索。”另,“永久和平”的提法,来自康德的另一篇文章《永久和平论》,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注
[8] “发言”的原文是“prendre la parole”,其中“prendre”是动词,意为“拿”“获得”等;“parole”是名词,意为“话”“说话”“发言(权)”等,所以该词组字面意思是“拿话”或“获得发言权”。下文中的“avoir la parole”则译为“有发言权”。——译注
[9] 这一段内容涉及的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译注
[10] “生来”原文为“par nature”,其中“nature”也译为“自然”,所以这句话也可译为“还是‘被自然’剥夺了理性”。——译注
[11] “自动转”原文为“marcheront toutes seules”,其中“marcher”既有(人)“行走”,也有(机器)“运转”的意思。在《论再生产》中,这个短语也译为“自动运转”。参见《论再生产》,吴子枫译,前引,第379页。另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页:“倘使每一无生命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或命令而自动进行工作……倘使每一个梭都能不假手于人力而自动地织布……匠师才用不到从属,奴隶主(家主)才可放弃奴隶。”——译注
[12] 参见第47页译注。——译注
[13] 指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前引。——译注
[14] 阿尔都塞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故事,比如1980年4月在意大利广播电台的访谈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讲过的另一个故事是橡树与驴的故事……
阿尔都塞: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列宁在瑞士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试图向人民解释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在俄国农村,一个半荒漠的地区,大约凌晨三点,一个叫伊万的人在家睡觉时,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了。他起床去开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门口有个叫格里高利的年轻人叫喊着:“有件可怕的事,真可怕……请跟我来。”年轻的格里高利把伊万带到一片田野,田野中间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一棵橡树。但那是晚上,所以看不太清。年轻的格里高利说:“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吗?他们把我的橡树还给驴子了。”但事实是,一头驴被拴在橡树上。伊万回答说:“你真是疯了,格里高利。只要改变你的想法,别说他们把橡树绑到驴身上,改说他们把驴拴在橡树上不就行了。”
该访谈的英文版可参见http://crisiscritique.org/blog.html。——译注
[15] 原文为“le chemin des chemins qui ne mènent nulle part”,在《列宁和哲学》中,这个表述用的是德文原文“der Holzweg der Holzwege”(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参见《列宁和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Maspero),“理论丛书”(« Théorie »),1969年,第14-15页,中译本参考《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前引。——译注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